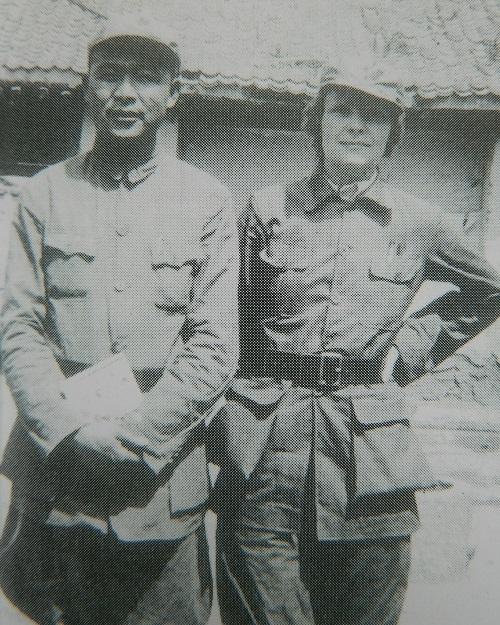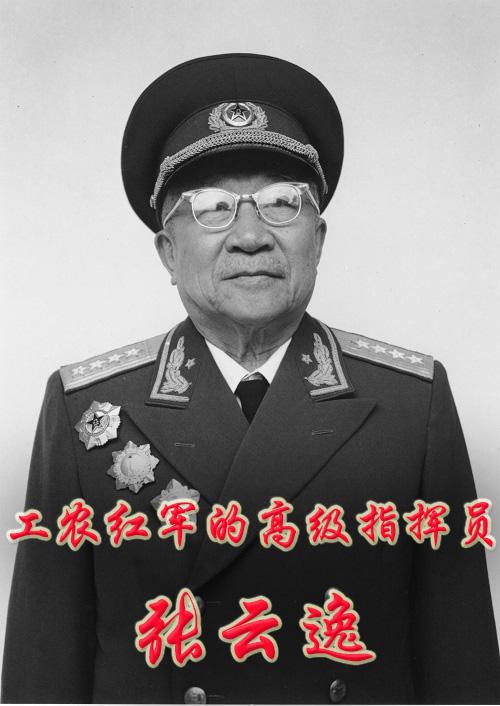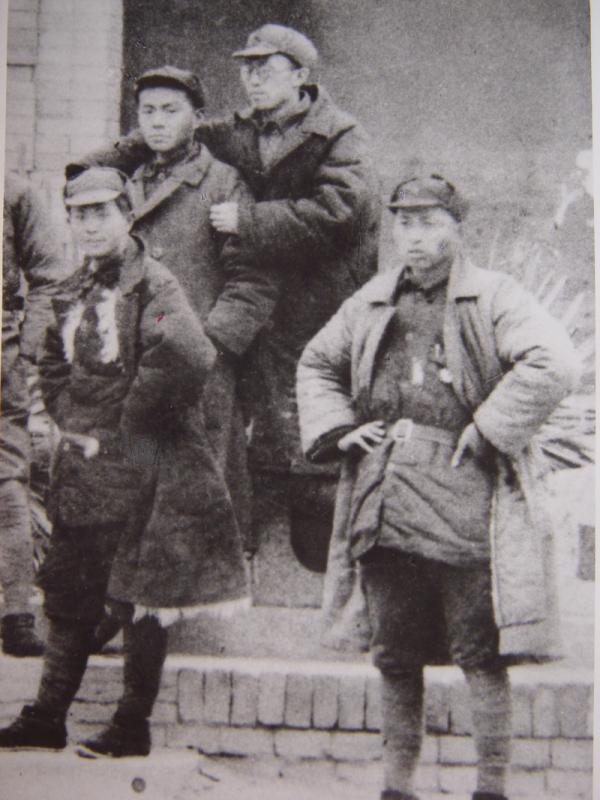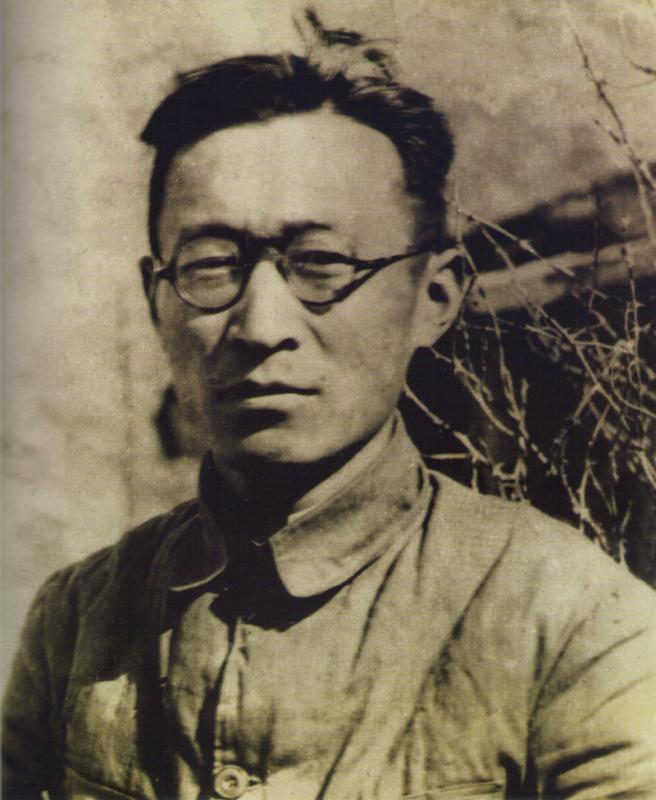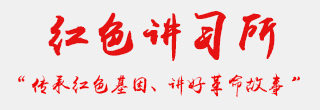父亲徐海东在长征中
发布时间:2019-02-22 11:24:51 浏览:
231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都快80岁了。父亲当年给我讲的红军长征的事迹,我记忆犹新。至此,我写下来,教育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红军精神,把红军的大旗一代一代传下去,抢我们的江山永不变色。
万里长征,军长主动让贤。行军打仗依然身先士卒。
父亲对我说:大别山区,遭到国民党军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许多地方成为了无人区。为了把红军赶尽灭绝,蒋介石的军队实施着一个“完全扑灭、永绝后患”的计划。他们的兵力增多到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采取筑碉堡、拉封锁线,并以“驻剿”、“追剿”相结合,搞什么“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做一网打尽之图”。他们分兵划区占领城镇和一些大的村镇,每个点上驻扎着守军“驻剿”,同时以机动部队“追剿”。并在黄(安)麻(城)公路沿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每隔五里、十里筑上碉堡,把守重要的通路。偌大的一个鄂豫皖苏区,被搞得七零八落。
自从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走后,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几经挫折,损兵折将,像一条游龙,在于涸的湖底挣扎着,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红军东转西走,已经没有了一个安稳之地了。
就在这个危难之时,1934年11月I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史册上,红军第二十五军是最先迈步长征的一支精兵。它对外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对内却说是“去打远游击”。寒冬已经到来,北国的风暴,正越过黄河,横扫中原大地。大别山的绿色,都已换成枯黄,刚刚落过一场雨,路面有的地方结起了冰,战士们的脚步走过,冰溶化了,脚下变成泥泞。每个红军战士,背着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背向着大别山,一步步跋涉。说是要远行,战士们还不知道是长征。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却是留恋那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离开过大别山。从前总是从鄂北到鄂东,从皖西到皖东。转来转去,都能看得到大别山。现在离开了大别山,许多人就像是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队列中,有七个女兵,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她们心事更重,有的人怕被留下,有的人又怕远离家乡。她们还要招呼着一群伤病员。伤病员中,有的坐担架,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拄着拐杖,随着部队缓缓前进。
我父亲走在全军的最后尾。心里也沉甸甸的。他明白,这次远行,是战略性的转移,就好像是寒冬就要到来,一群大雁向南飞,去找寻一个过冬的地方。从1934年2月。党中央就来信,要红军向外发展,原因是经过敌人的五次“围剿”,大别山区已经是民穷财尽,红军要生存要发展,只有离开大别山。后来,党中央又派程子华来,要红军尽早转移出大别山。到什么地方去呢?中央只有四条原则的指示: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富裕的地区。父亲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他觉得,中国的地方虽然大,红军要真正找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地区,难呢!凡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是山区。可是山区都是穷乡僻壤,给养困难啊!平原物质条件好,不是红军去的好地方,山区又不能养兵,到底向哪里走呢?……
父亲说:行军路上,他不论是步行还是坐在马上,都心神不宁。想到几年前,大别山的红军像春雨绵绵的山花,一天天红火,走的是上坡路;如今虽然不能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正像这寒冬一样,冷风凄凉,行无目标。住无安息之处。这三千多人的一支部队,孤立无援,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是令人担心的啊!
出发之前,父亲已经从军长变成为副军长,论说责任比当军长小了,可是,这是自己给自己降的职。他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是个师长,又进过黄埔军校,一定比自己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人能干,他便主动向省委提出申请,自己当副的,要程子华当正的。省委会上,大家出于对中央派来的人的信赖,就通过了父亲的建议。
父亲是诚心让位,让强过自己的人当第一把手,自己甘做配角。他想的是红军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得失,可是,传达下去,许多人不理解。有的干部想不通,有的人还认定父亲犯了什么事。议论纷纭:“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
“该不是哪个‘老三’(指肃反中被捕的所谓“第三党”)又咬了他一口!”
“他出身好,全身那么多的枪伤,那才是‘老三’咬的呢。没有他就没有红二十五军,他……”
“这领兵打仗的事,怎么能随便让位?”
议论纷纷,话传到书记徐宝珊耳边。这位代理省委书记,自从沈泽民病故后按任书记的工作,他每天也是病魔缠身,强作健康的人,随军行动。虽然军事上没有多少经验。但是,他为人正直,革命精神好。对父亲这样的战将,十分敬佩和爱戴。他昕到那些议论,就向人们解释,不是徐海东有什么问题,是他党性好,是主动让位的。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一天,行军的路上,徐宝珊见到我父亲,便从骡子上跳下来,和我父亲并肩走着,笑着问:“海东啊,你听到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啦。省委可不是这么看呀,你不当军长当副军长,不是你工作不好,打仗不好,更不是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父亲笑着打断了省委书记的话,“我最不爱听那些闲话,说是犯错误,咱们不红脸,当军长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是官是兵,都打仗,为革命,还分什么正副高低呀!”
徐宝珊熟悉我父亲,知道他党性很强,一心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职务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伤住院,回来后团长的位置有人了,一时难以安排他的工作,他就主动提出当副团长。如今这副军长的位置,又是他自己提出的呀。省委会仓促的决定,使这位书记有些不安。
“宝珊啊,你不要担心我,多保重身子。”父亲怕省委书记累着,叫他快骑上骡子。
徐宝珊还是吃力地走着,气喘吁吁地说:“海东,你是好同志啊,我是放心你呀,你可要……”
“宝珊,你是了解我的嘛,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连他娘的一个村长也当不上呢。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工!”说着又嘿嘿一笑。他和自己的警卫员一齐动手,硬是把省委书记扶上骡子,接若向骡子的屁股抽了一马鞭,那骡子快步小跑开了。这才算是结束了这次同志间的谈话。这也是父亲和徐宝珊最后的一次亲切交谈。四个月之后—1935年5月徐宝珊在任鄂豫陕省委书记刚一个月,就病故在陕南的龙驹寨了。父亲终生都不忘长征开始和徐宝珊的那次谈话。他曾经对我说:“徐宝珊是一位好同志,他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病故后,他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领导我们坚持了大别山的斗争,又领导我们开始长征,功不可没。他和沈泽民同志一样,是大别山人民革命、是红军第二十五军征战的一面旗帜。”
父亲说,红二十五军这次战略转移,在部队战士中只说是“打远游击”,对团以上的干部才说要“创造新的根据地”。远到什么地方?新的根据地又在哪里,谁都说不清楚。只是在师以上的干部中,才明确提出:第一步行动计划,是西向桐柏山区。然而,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关,却很快就发觉了红二十五军的去向。红二十五军刚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之前,蒋介石的追兵就出动了。总兵力有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分为“跟踪追击”和“迎头堵截”。据说,蒋介石得知我父亲部(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改为副军长)“流窜”出大别山西进,惊恐得很。很怕这个“徐老虎”像两年前的徐向前那样,从大别山“流窜”到大巴山下,在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又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红区,又发展起近八万人的红军。“要穷追不舍,直到把徐海东部彻底消灭!”这是国民党军的决心和口号。
红军二十五军是生,是死,一时成为中原战场的一个焦点。
白军千军万马追堵,一支不满三千人的红军,在风雨中拼搏。前者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有充足的粮弹;后者是步枪、大刀和手榴弹,每人只有两双草鞋和两天的干粮。父亲从部队开始出征,就带兵先行。他率领着一个手枪排,负责侦察、探路。常常是夜晚行军,白天债探敌情、地形和民情。新军长刚来,兵不熟,将不熟,他这个老军长,深知自己应该行军走在前,打仗冲在前。几天几夜下来,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但是,敌情严重,他感到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掌握好敌情,每天都向手枪排长说:“马虎一点,就要全军遭殃,明白吗?”“腿要长,耳目要灵。哪个不听话,误了事,我要追究责任!”
“军长,误了事,先杀我的头。”
“要知道,个人的脑袋掉了,那只是一个人,我们身后有三千几百人呀!”
这个手枪排,是支小小的精兵分队。每个战士都是从连队中挑选出来的,个头高,精明强干,枪法好,有实战经验。他们一色的黑军服,每人一把短枪,外加一把鬼头大刀。他们练出了一身过硬的行走、夜战本领。紧急情况下,一个小时,能跑二十多里路。在红军中号称能跑、能战、能应急的“飞毛腿”。父亲从在大别山区,就十分重视培养这支小部队。侦察、夜摸、捉俘虏、通信联络、必要时打冲锋。这天夜晚,父亲正为摸不准敌人的行踪而焦虑,手枪排的排长飞跑来报告:敌情紧张,军部要他快快前去。父亲一听,提着马鞭,出了屋子,跃身上马,摸黑飞向军部驻地。
路口旁边,有一座小村庄。是先头部队经过的地方。父亲和他的战马,是原路返回。军长、政委、参谋长正在村中一家小屋里的马灯下围坐,看着地图议论行动方案。大家一见父亲到来,连忙招呼他坐下。
父亲问:“怎么样?情况有变化?”
政委说:“情况大变,敌人四面出击。看来我们进桐柏山的计划难实现哟!”
参谋接下来讲着敌情,据侦查,敌军发现了红军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的企图,驻扎在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六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都出动了。驻扎在开封的六十师正开往朱阳关,控制了通往陕南的大道。红军如今是进退两难了。就地打游击,一是地理环境对我不利,二是包围圈会越来越紧,前途就像几条小鱼游戏于一只小小的脸盆里;若想重返大别山区,后路又全都被敌人堵住了。眼前只有前进是上策。可是,前进到什么地区好呢?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政委吴焕先见我父亲不言语,就转头向他问:“海东,你的想法呢?”
父亲不是不言语,是没有想好。这几天来,他就反复思考,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眼下生存发展之地,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着汉水,群众条件也不了解。眼下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这个桐柏山区,是绝对进不得了。他认为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伏牛山区。可是,对那里的情况,自己不怎么清楚,只是从地理环境和敌人的当前的兵力布置上,认定进入伏牛山区比进入桐柏山区有利。父亲见政委点名要他表态,他就说:“敌人不让我们进桐柏山,那就进伏牛山好咧。”他的话说得虽然轻松,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回事。
大家都同时把目光转向他。是对这位老军长的信任,又是对他的想法赞赏。他总是在困境中,勇于提出带转折性的行动方案。大家纳闷的是,红军从出征以来,已经连续走了七八个黑夜,若是又长途跋涉,战士们能支持下来吗?前边路上敌人层层重兵把守,我们将如何冲出去?伏牛山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会场一时沉闷了。父亲以为大家对他的建议有保留,就嘿嘿笑笑,打破了会场的沉闷,他接下来说:“我想的还不那么成熟,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不,你的意见很值得好好议议。”吴焕先首先表示赞赏。这位年轻的政委,最大的一个长处,是能倾听和吸取有益的建议。他性格坚强,思路敏捷,多谋善断,常常在不利的情况下,稳定情绪,依靠集体的智慧找出出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我们这些‘山大王’,总是离不开山的哟,桐柏山进去难,就来个出敌不备,进伏牛山。”父亲数着指头,把敌人的情况摆出了几条。话语刚打住,政委又说:“这下一着棋走得好不好,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海东同志的意见,是个方案。”
“我也想不进桐柏山区,”新军民程子华说,“敌变我变。就是要去敌人一个想不到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暂时的喘息之机。前进的路程可能是艰难的,去伏牛山区要比进桐柏的路远多了,可是事到如今,舍近求远,是一个上策。我们虽然疲惫些,这些天的行军,我看到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走不散、拖得起的部队。敌人比我们还疲惫,要想追踪我们,难哩!”程军长讲话声音不高,一句句深人人心。看来这位新军长,胸中有数,也已有了放弃原行动计划的打算。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夜深人不静,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红军指挥部里,紧张地讨论着新的行动计划,大家围绕着如何摆脱敌人,进入伏牛山,走出困境,制定了新的行军作战方案。大敌当前,分歧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统一。
散会时,军长和政委都向我父亲说,他们今晚要走前头了,让我父亲压后。这样的安排,不说父亲也明白,是要他从前卫变后尾,路上可以略略松快一点,省心省力。父亲不答应。他觉得,程军长新到,身体也不是那么强壮,不能叫他带头走。自己是副军长,从职务上来说,行军打仗,都应该在前头。父亲也不便把话讲得那么明确,笑呵呵地说:“军长啊,你可知道咧,行军在前头,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自由呢。早到目的地是早休息,走在后边晚休息啊,我是想早早地休息呀!”说着快快走开了。
按照会议统一的方案,红军派出一个团,向枣阳县城方向佯装攻击,把敌人调动了一下,迷惑了一下,红军主力悄悄突破他们设在保安寨一带的防线,向方城东北许(昌)南(阳)公路插出去……
父亲带领着一个前卫团,白天驻军,夜晚行军。抢占隘路,侦探敌情,为后边的大部队开路,向伏牛山区进军。他白天少睡,夜晚难眠。实在走不动了,才骑上战马,打一个盹,休息一下,又跳下马来和战士们一路行走。作为高级指挥员,行军骑马甚至于坐抬子,不是当官特殊,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需要。只有保证指挥员精力充沛,才能使他们在指挥作战时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父亲却认为,他的精力永远是过剩的,只要枪声一响,他三天三夜不合眼,也能支持下来。所以,正常情况下行军,他的战骑,总是让给伤病员。再不然,就是小马倌拉着马跟随他前进。
在向伏牛山区前进的路上,父亲又是四个黑夜带头步行。两只眼睛熬得又红又肿。每天在大部队休息时,他仍是带着疲倦的神色,强打着精神,骑马转回军指挥部和军长、政委会面,交换意见。这天,新任军长程子华见我父亲说着话睡了,知道他太劳累,等他睁眼清醒时,向他说,今天夜行军,他们要换个位置,要徐海东走后卫。父亲嘿嘿一笑,摇头又摆手,连声说:“不行,不行!”政委吴焕先看军长和副军长争着要带前卫团,这次便站在军长一边说:“海东,今天应该换换了,你走后卫,我和子华走前卫。”说着向军长叫了一声:“走啊,到前边去!前边有好吃的哟。”这位政委,像娃娃玩似的,笑眯眯的,向我父亲一挥手,走咧。军长也就起身,笑嘻嘻地向我父亲挥手告别了。看来会前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父亲此时也只得从命。
其实,行军途中,前与后,谁都不比谁少走路,可是,紧急情况下的战斗行军,走在后边的指挥员,要比走在前边的指挥员精神上松快些。他可以不必多分心去了解敌情,不必担心走错了路线。父亲这时也觉得实在是疲劳,队伍一出发,就骑上马,迷迷糊糊打起盹来。马背上睡觉对他说来,要比睡在床上都安心。可是,这一次他只睡了多半小时,就从马上跳了下来。一来是,天气骤然变冷,两只套着草鞋的脚冻得发木,二来是,队伍中拄棍子的伤病号很多,路途泥泞,不住地有人摔倒。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忍心骑在马上。雨越下越大,跌倒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他的警卫员,把一个跌倒的病号扶上马背,自己拄着那病号的棍子,缓缓地向前走。
这一夜的路程,真是艰难极了。天上浇雨水,地上是泥水,在经过一段鱼背似的路面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摔倒过,一个个成了泥人。走到后半夜,雨更大了,路过一个村庄,前边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口令一下,许多人跑到路旁老乡的房前、屋后和草棚里躲雨去了。警卫员也把我父亲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此机会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响哨子,要继续前进。父亲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他要警卫员快快督促同志们出来上路。雨仍在不停地下,战士们真不想离开这村庄。
有的人一边走,一边骂天骂地。
“他妈的,这老天跟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父亲拄着一根棍子,一边叫,一边走。他估计这一停下,可能有些人睡下了,便挨家挨户去查看。果然,每一家都有战士睡着了。有的在屋里,有的在房檐底下,他们东倒西歪,听到副军长大声呼叫,这才迅速爬起来,去追赶队伍。徐海东正对一个连长发火,听说后卫团的团长和政委还睡在屋里,便气冲冲地走进去,挥着手上的棍子,先把团长打起,又把政委打起,边打边骂……就这样,他从这个村庄里撵出了二百多人。许多年以后,一个挨过我父亲棍子的干部感激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这个雨夜,父亲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前边是敌人,后头是追兵,迟缓就要失去跳出重围的时机,躺着不走,就是自毙!他敬佩新军长和老政委的果断。可是由于自己打了人,一上路,心里又觉得十分不安。他暗暗怨恨自己:为什么又犯老毛病,拿棍子打人呢?这老毛病也真是难改啊!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把手里的棍子使劲向路旁一扔,像是要与那“老毛病”绝交似的……
天蒙蒙发亮,雨渐渐小了。队伍正在急速前进。口令不时由前向后传:“跟上,跟上,不能掉队!”这声音预示着情况仍然危险。父亲早就把马让给了伤病员,正艰难地一步步向前迈。突然,他发现路旁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哼哼唷唷,走过去一问,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父亲朝前看了看,一拐一拐的伤病员真不少,往后看去,也几乎都是些行走困难的伤病员。他在担架旁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负过十儿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父亲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路。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父亲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不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不要喊,躺着。”
“放下,快放下我!”
“听话,不要叫。”父亲只重复着这句话。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电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父亲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东西,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嘿嘿,娘卖皮的,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
“那不是!”父亲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父亲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同志们顿时领会了老军民的意思。“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像老虎一样,爱山林、靠山林、离不开山林。眼前速三个山头,对他来说好比增加了三个团的援兵!
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后怕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父亲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他的人,当成玩笑,当作幽默,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哲理。父亲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11月26日拂晓,部队长途行军,来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恰巧遇到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刺骨,雨雪交加。战士们衣服本来单薄,此时真是饥寒交迫,疲乏不堪。全军正准备经由七里岗过公路的时候,敌军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抢先占领了七里岗、砚山铺一线有利的地形,突然向行进中的红军发动进攻。父亲随后卫部队行走,只顾顶风冒雨前进,并没有应战的思想准备,听到枪声,连忙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此时战士们冻僵的手指都拉不开枪栓了。在慌张的撤退中,敌人又从两翼包围上来。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走在先头部队中的军政委吴焕先,高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风雨中,战士们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胆怯的冷静了,共产党员们带头应战。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一把鬼头大刀,这时就抽出大刀,与敌人展开拼搏。吴焕先也随手抽出交通员身后的那把大刀,呼喊着向敌人冲去。他一边跑,一选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滚雪球似的,向前爬,向前滚,和敌人混战在雨雪中。在后卫队的父亲,从枪声中和传呼的口令,知道了前头的情况,他马上带领后卫部队,跑步向前增援。路过一小村庄外,战士们见到一堆小草垛被点燃了,围上去烘烘僵硬的手,烘一烘结冰的枪,又向前跑去。
敌军本想借风雪天气和红军疲惫不堪,给红军一个突然袭击,致红军于死地,没想到红军会凭借着几个村庄和一些地形,殊死搏斗。从拂晓到黄昏,三千多人的红军,与近万人的敌军拼搏了一天,父亲见天色已晚,认定敌人采取的是包围战术,想一点一点压缩包围圈,困死、冻死红军。他和吴焕先一合谋,决定在夜晚冲出包围圈。
“我来带领突击队,”吴焕先说,“你和军长押后……”
“不,还是我带突击队,”父亲不等政委把话说完,和过去一样,又和政委争起了突击队的任务。
吴焕先了解我父亲的脾气,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是不让步、不后退的。打仗在前、吃苦在先,是父亲的风格。危机的关头,常常是他扭转战局。在场的领导人,都把目光投向我父亲。父亲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决心与战斗方案,当即亲自组织了几十名轻机枪手,作为冲锋队。入夜,趁着大风大雪,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第二天,当敌人还在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向东还是向西时,父亲率领红军已远走高飞,消失在白茫茫的伏牛山里。
万里长征,军长主动让贤。行军打仗依然身先士卒。
父亲对我说:大别山区,遭到国民党军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许多地方成为了无人区。为了把红军赶尽灭绝,蒋介石的军队实施着一个“完全扑灭、永绝后患”的计划。他们的兵力增多到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采取筑碉堡、拉封锁线,并以“驻剿”、“追剿”相结合,搞什么“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做一网打尽之图”。他们分兵划区占领城镇和一些大的村镇,每个点上驻扎着守军“驻剿”,同时以机动部队“追剿”。并在黄(安)麻(城)公路沿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每隔五里、十里筑上碉堡,把守重要的通路。偌大的一个鄂豫皖苏区,被搞得七零八落。
自从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走后,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几经挫折,损兵折将,像一条游龙,在于涸的湖底挣扎着,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红军东转西走,已经没有了一个安稳之地了。
就在这个危难之时,1934年11月I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史册上,红军第二十五军是最先迈步长征的一支精兵。它对外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对内却说是“去打远游击”。寒冬已经到来,北国的风暴,正越过黄河,横扫中原大地。大别山的绿色,都已换成枯黄,刚刚落过一场雨,路面有的地方结起了冰,战士们的脚步走过,冰溶化了,脚下变成泥泞。每个红军战士,背着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背向着大别山,一步步跋涉。说是要远行,战士们还不知道是长征。他们嘴上不说,心中却是留恋那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离开过大别山。从前总是从鄂北到鄂东,从皖西到皖东。转来转去,都能看得到大别山。现在离开了大别山,许多人就像是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队列中,有七个女兵,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她们心事更重,有的人怕被留下,有的人又怕远离家乡。她们还要招呼着一群伤病员。伤病员中,有的坐担架,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拄着拐杖,随着部队缓缓前进。
我父亲走在全军的最后尾。心里也沉甸甸的。他明白,这次远行,是战略性的转移,就好像是寒冬就要到来,一群大雁向南飞,去找寻一个过冬的地方。从1934年2月。党中央就来信,要红军向外发展,原因是经过敌人的五次“围剿”,大别山区已经是民穷财尽,红军要生存要发展,只有离开大别山。后来,党中央又派程子华来,要红军尽早转移出大别山。到什么地方去呢?中央只有四条原则的指示: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富裕的地区。父亲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他觉得,中国的地方虽然大,红军要真正找到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地区,难呢!凡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是山区。可是山区都是穷乡僻壤,给养困难啊!平原物质条件好,不是红军去的好地方,山区又不能养兵,到底向哪里走呢?……
父亲说:行军路上,他不论是步行还是坐在马上,都心神不宁。想到几年前,大别山的红军像春雨绵绵的山花,一天天红火,走的是上坡路;如今虽然不能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正像这寒冬一样,冷风凄凉,行无目标。住无安息之处。这三千多人的一支部队,孤立无援,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是令人担心的啊!
出发之前,父亲已经从军长变成为副军长,论说责任比当军长小了,可是,这是自己给自己降的职。他听说程子华在中央红军是个师长,又进过黄埔军校,一定比自己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人能干,他便主动向省委提出申请,自己当副的,要程子华当正的。省委会上,大家出于对中央派来的人的信赖,就通过了父亲的建议。
父亲是诚心让位,让强过自己的人当第一把手,自己甘做配角。他想的是红军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得失,可是,传达下去,许多人不理解。有的干部想不通,有的人还认定父亲犯了什么事。议论纷纭:“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
“该不是哪个‘老三’(指肃反中被捕的所谓“第三党”)又咬了他一口!”
“他出身好,全身那么多的枪伤,那才是‘老三’咬的呢。没有他就没有红二十五军,他……”
“这领兵打仗的事,怎么能随便让位?”
议论纷纷,话传到书记徐宝珊耳边。这位代理省委书记,自从沈泽民病故后按任书记的工作,他每天也是病魔缠身,强作健康的人,随军行动。虽然军事上没有多少经验。但是,他为人正直,革命精神好。对父亲这样的战将,十分敬佩和爱戴。他昕到那些议论,就向人们解释,不是徐海东有什么问题,是他党性好,是主动让位的。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一天,行军的路上,徐宝珊见到我父亲,便从骡子上跳下来,和我父亲并肩走着,笑着问:“海东啊,你听到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啦。省委可不是这么看呀,你不当军长当副军长,不是你工作不好,打仗不好,更不是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父亲笑着打断了省委书记的话,“我最不爱听那些闲话,说是犯错误,咱们不红脸,当军长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是官是兵,都打仗,为革命,还分什么正副高低呀!”
徐宝珊熟悉我父亲,知道他党性很强,一心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职务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伤住院,回来后团长的位置有人了,一时难以安排他的工作,他就主动提出当副团长。如今这副军长的位置,又是他自己提出的呀。省委会仓促的决定,使这位书记有些不安。
“宝珊啊,你不要担心我,多保重身子。”父亲怕省委书记累着,叫他快骑上骡子。
徐宝珊还是吃力地走着,气喘吁吁地说:“海东,你是好同志啊,我是放心你呀,你可要……”
“宝珊,你是了解我的嘛,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连他娘的一个村长也当不上呢。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工!”说着又嘿嘿一笑。他和自己的警卫员一齐动手,硬是把省委书记扶上骡子,接若向骡子的屁股抽了一马鞭,那骡子快步小跑开了。这才算是结束了这次同志间的谈话。这也是父亲和徐宝珊最后的一次亲切交谈。四个月之后—1935年5月徐宝珊在任鄂豫陕省委书记刚一个月,就病故在陕南的龙驹寨了。父亲终生都不忘长征开始和徐宝珊的那次谈话。他曾经对我说:“徐宝珊是一位好同志,他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病故后,他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领导我们坚持了大别山的斗争,又领导我们开始长征,功不可没。他和沈泽民同志一样,是大别山人民革命、是红军第二十五军征战的一面旗帜。”
父亲说,红二十五军这次战略转移,在部队战士中只说是“打远游击”,对团以上的干部才说要“创造新的根据地”。远到什么地方?新的根据地又在哪里,谁都说不清楚。只是在师以上的干部中,才明确提出:第一步行动计划,是西向桐柏山区。然而,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关,却很快就发觉了红二十五军的去向。红二十五军刚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之前,蒋介石的追兵就出动了。总兵力有五个支队共四十多个团,分为“跟踪追击”和“迎头堵截”。据说,蒋介石得知我父亲部(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改为副军长)“流窜”出大别山西进,惊恐得很。很怕这个“徐老虎”像两年前的徐向前那样,从大别山“流窜”到大巴山下,在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又造成了一个更大的红区,又发展起近八万人的红军。“要穷追不舍,直到把徐海东部彻底消灭!”这是国民党军的决心和口号。
红军二十五军是生,是死,一时成为中原战场的一个焦点。
白军千军万马追堵,一支不满三千人的红军,在风雨中拼搏。前者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有充足的粮弹;后者是步枪、大刀和手榴弹,每人只有两双草鞋和两天的干粮。父亲从部队开始出征,就带兵先行。他率领着一个手枪排,负责侦察、探路。常常是夜晚行军,白天债探敌情、地形和民情。新军长刚来,兵不熟,将不熟,他这个老军长,深知自己应该行军走在前,打仗冲在前。几天几夜下来,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但是,敌情严重,他感到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掌握好敌情,每天都向手枪排长说:“马虎一点,就要全军遭殃,明白吗?”“腿要长,耳目要灵。哪个不听话,误了事,我要追究责任!”
“军长,误了事,先杀我的头。”
“要知道,个人的脑袋掉了,那只是一个人,我们身后有三千几百人呀!”
这个手枪排,是支小小的精兵分队。每个战士都是从连队中挑选出来的,个头高,精明强干,枪法好,有实战经验。他们一色的黑军服,每人一把短枪,外加一把鬼头大刀。他们练出了一身过硬的行走、夜战本领。紧急情况下,一个小时,能跑二十多里路。在红军中号称能跑、能战、能应急的“飞毛腿”。父亲从在大别山区,就十分重视培养这支小部队。侦察、夜摸、捉俘虏、通信联络、必要时打冲锋。这天夜晚,父亲正为摸不准敌人的行踪而焦虑,手枪排的排长飞跑来报告:敌情紧张,军部要他快快前去。父亲一听,提着马鞭,出了屋子,跃身上马,摸黑飞向军部驻地。
路口旁边,有一座小村庄。是先头部队经过的地方。父亲和他的战马,是原路返回。军长、政委、参谋长正在村中一家小屋里的马灯下围坐,看着地图议论行动方案。大家一见父亲到来,连忙招呼他坐下。
父亲问:“怎么样?情况有变化?”
政委说:“情况大变,敌人四面出击。看来我们进桐柏山的计划难实现哟!”
参谋接下来讲着敌情,据侦查,敌军发现了红军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的企图,驻扎在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四十六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都出动了。驻扎在开封的六十师正开往朱阳关,控制了通往陕南的大道。红军如今是进退两难了。就地打游击,一是地理环境对我不利,二是包围圈会越来越紧,前途就像几条小鱼游戏于一只小小的脸盆里;若想重返大别山区,后路又全都被敌人堵住了。眼前只有前进是上策。可是,前进到什么地区好呢?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政委吴焕先见我父亲不言语,就转头向他问:“海东,你的想法呢?”
父亲不是不言语,是没有想好。这几天来,他就反复思考,桐柏山区,并非是红军眼下生存发展之地,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着汉水,群众条件也不了解。眼下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这个桐柏山区,是绝对进不得了。他认为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伏牛山区。可是,对那里的情况,自己不怎么清楚,只是从地理环境和敌人的当前的兵力布置上,认定进入伏牛山区比进入桐柏山区有利。父亲见政委点名要他表态,他就说:“敌人不让我们进桐柏山,那就进伏牛山好咧。”他的话说得虽然轻松,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回事。
大家都同时把目光转向他。是对这位老军长的信任,又是对他的想法赞赏。他总是在困境中,勇于提出带转折性的行动方案。大家纳闷的是,红军从出征以来,已经连续走了七八个黑夜,若是又长途跋涉,战士们能支持下来吗?前边路上敌人层层重兵把守,我们将如何冲出去?伏牛山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会场一时沉闷了。父亲以为大家对他的建议有保留,就嘿嘿笑笑,打破了会场的沉闷,他接下来说:“我想的还不那么成熟,只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不,你的意见很值得好好议议。”吴焕先首先表示赞赏。这位年轻的政委,最大的一个长处,是能倾听和吸取有益的建议。他性格坚强,思路敏捷,多谋善断,常常在不利的情况下,稳定情绪,依靠集体的智慧找出出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我们这些‘山大王’,总是离不开山的哟,桐柏山进去难,就来个出敌不备,进伏牛山。”父亲数着指头,把敌人的情况摆出了几条。话语刚打住,政委又说:“这下一着棋走得好不好,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海东同志的意见,是个方案。”
“我也想不进桐柏山区,”新军民程子华说,“敌变我变。就是要去敌人一个想不到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暂时的喘息之机。前进的路程可能是艰难的,去伏牛山区要比进桐柏的路远多了,可是事到如今,舍近求远,是一个上策。我们虽然疲惫些,这些天的行军,我看到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走不散、拖得起的部队。敌人比我们还疲惫,要想追踪我们,难哩!”程军长讲话声音不高,一句句深人人心。看来这位新军长,胸中有数,也已有了放弃原行动计划的打算。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夜深人不静,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红军指挥部里,紧张地讨论着新的行动计划,大家围绕着如何摆脱敌人,进入伏牛山,走出困境,制定了新的行军作战方案。大敌当前,分歧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统一。
散会时,军长和政委都向我父亲说,他们今晚要走前头了,让我父亲压后。这样的安排,不说父亲也明白,是要他从前卫变后尾,路上可以略略松快一点,省心省力。父亲不答应。他觉得,程军长新到,身体也不是那么强壮,不能叫他带头走。自己是副军长,从职务上来说,行军打仗,都应该在前头。父亲也不便把话讲得那么明确,笑呵呵地说:“军长啊,你可知道咧,行军在前头,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自由呢。早到目的地是早休息,走在后边晚休息啊,我是想早早地休息呀!”说着快快走开了。
按照会议统一的方案,红军派出一个团,向枣阳县城方向佯装攻击,把敌人调动了一下,迷惑了一下,红军主力悄悄突破他们设在保安寨一带的防线,向方城东北许(昌)南(阳)公路插出去……
父亲带领着一个前卫团,白天驻军,夜晚行军。抢占隘路,侦探敌情,为后边的大部队开路,向伏牛山区进军。他白天少睡,夜晚难眠。实在走不动了,才骑上战马,打一个盹,休息一下,又跳下马来和战士们一路行走。作为高级指挥员,行军骑马甚至于坐抬子,不是当官特殊,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需要。只有保证指挥员精力充沛,才能使他们在指挥作战时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父亲却认为,他的精力永远是过剩的,只要枪声一响,他三天三夜不合眼,也能支持下来。所以,正常情况下行军,他的战骑,总是让给伤病员。再不然,就是小马倌拉着马跟随他前进。
在向伏牛山区前进的路上,父亲又是四个黑夜带头步行。两只眼睛熬得又红又肿。每天在大部队休息时,他仍是带着疲倦的神色,强打着精神,骑马转回军指挥部和军长、政委会面,交换意见。这天,新任军长程子华见我父亲说着话睡了,知道他太劳累,等他睁眼清醒时,向他说,今天夜行军,他们要换个位置,要徐海东走后卫。父亲嘿嘿一笑,摇头又摆手,连声说:“不行,不行!”政委吴焕先看军长和副军长争着要带前卫团,这次便站在军长一边说:“海东,今天应该换换了,你走后卫,我和子华走前卫。”说着向军长叫了一声:“走啊,到前边去!前边有好吃的哟。”这位政委,像娃娃玩似的,笑眯眯的,向我父亲一挥手,走咧。军长也就起身,笑嘻嘻地向我父亲挥手告别了。看来会前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父亲此时也只得从命。
其实,行军途中,前与后,谁都不比谁少走路,可是,紧急情况下的战斗行军,走在后边的指挥员,要比走在前边的指挥员精神上松快些。他可以不必多分心去了解敌情,不必担心走错了路线。父亲这时也觉得实在是疲劳,队伍一出发,就骑上马,迷迷糊糊打起盹来。马背上睡觉对他说来,要比睡在床上都安心。可是,这一次他只睡了多半小时,就从马上跳了下来。一来是,天气骤然变冷,两只套着草鞋的脚冻得发木,二来是,队伍中拄棍子的伤病号很多,路途泥泞,不住地有人摔倒。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忍心骑在马上。雨越下越大,跌倒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他的警卫员,把一个跌倒的病号扶上马背,自己拄着那病号的棍子,缓缓地向前走。
这一夜的路程,真是艰难极了。天上浇雨水,地上是泥水,在经过一段鱼背似的路面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摔倒过,一个个成了泥人。走到后半夜,雨更大了,路过一个村庄,前边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口令一下,许多人跑到路旁老乡的房前、屋后和草棚里躲雨去了。警卫员也把我父亲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此机会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响哨子,要继续前进。父亲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他要警卫员快快督促同志们出来上路。雨仍在不停地下,战士们真不想离开这村庄。
有的人一边走,一边骂天骂地。
“他妈的,这老天跟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父亲拄着一根棍子,一边叫,一边走。他估计这一停下,可能有些人睡下了,便挨家挨户去查看。果然,每一家都有战士睡着了。有的在屋里,有的在房檐底下,他们东倒西歪,听到副军长大声呼叫,这才迅速爬起来,去追赶队伍。徐海东正对一个连长发火,听说后卫团的团长和政委还睡在屋里,便气冲冲地走进去,挥着手上的棍子,先把团长打起,又把政委打起,边打边骂……就这样,他从这个村庄里撵出了二百多人。许多年以后,一个挨过我父亲棍子的干部感激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这个雨夜,父亲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前边是敌人,后头是追兵,迟缓就要失去跳出重围的时机,躺着不走,就是自毙!他敬佩新军长和老政委的果断。可是由于自己打了人,一上路,心里又觉得十分不安。他暗暗怨恨自己:为什么又犯老毛病,拿棍子打人呢?这老毛病也真是难改啊!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把手里的棍子使劲向路旁一扔,像是要与那“老毛病”绝交似的……
天蒙蒙发亮,雨渐渐小了。队伍正在急速前进。口令不时由前向后传:“跟上,跟上,不能掉队!”这声音预示着情况仍然危险。父亲早就把马让给了伤病员,正艰难地一步步向前迈。突然,他发现路旁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哼哼唷唷,走过去一问,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父亲朝前看了看,一拐一拐的伤病员真不少,往后看去,也几乎都是些行走困难的伤病员。他在担架旁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负过十儿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父亲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路。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父亲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不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不要喊,躺着。”
“放下,快放下我!”
“听话,不要叫。”父亲只重复着这句话。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电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父亲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东西,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嘿嘿,娘卖皮的,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
“那不是!”父亲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父亲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同志们顿时领会了老军民的意思。“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像老虎一样,爱山林、靠山林、离不开山林。眼前速三个山头,对他来说好比增加了三个团的援兵!
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后怕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父亲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他的人,当成玩笑,当作幽默,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哲理。父亲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11月26日拂晓,部队长途行军,来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恰巧遇到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刺骨,雨雪交加。战士们衣服本来单薄,此时真是饥寒交迫,疲乏不堪。全军正准备经由七里岗过公路的时候,敌军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抢先占领了七里岗、砚山铺一线有利的地形,突然向行进中的红军发动进攻。父亲随后卫部队行走,只顾顶风冒雨前进,并没有应战的思想准备,听到枪声,连忙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此时战士们冻僵的手指都拉不开枪栓了。在慌张的撤退中,敌人又从两翼包围上来。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走在先头部队中的军政委吴焕先,高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决不能后退!”风雨中,战士们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胆怯的冷静了,共产党员们带头应战。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一把鬼头大刀,这时就抽出大刀,与敌人展开拼搏。吴焕先也随手抽出交通员身后的那把大刀,呼喊着向敌人冲去。他一边跑,一选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滚雪球似的,向前爬,向前滚,和敌人混战在雨雪中。在后卫队的父亲,从枪声中和传呼的口令,知道了前头的情况,他马上带领后卫部队,跑步向前增援。路过一小村庄外,战士们见到一堆小草垛被点燃了,围上去烘烘僵硬的手,烘一烘结冰的枪,又向前跑去。
敌军本想借风雪天气和红军疲惫不堪,给红军一个突然袭击,致红军于死地,没想到红军会凭借着几个村庄和一些地形,殊死搏斗。从拂晓到黄昏,三千多人的红军,与近万人的敌军拼搏了一天,父亲见天色已晚,认定敌人采取的是包围战术,想一点一点压缩包围圈,困死、冻死红军。他和吴焕先一合谋,决定在夜晚冲出包围圈。
“我来带领突击队,”吴焕先说,“你和军长押后……”
“不,还是我带突击队,”父亲不等政委把话说完,和过去一样,又和政委争起了突击队的任务。
吴焕先了解我父亲的脾气,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是不让步、不后退的。打仗在前、吃苦在先,是父亲的风格。危机的关头,常常是他扭转战局。在场的领导人,都把目光投向我父亲。父亲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决心与战斗方案,当即亲自组织了几十名轻机枪手,作为冲锋队。入夜,趁着大风大雪,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第二天,当敌人还在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向东还是向西时,父亲率领红军已远走高飞,消失在白茫茫的伏牛山里。
更多推荐
更多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都快80岁了。父亲当年给我讲的红军长征的事迹,我记忆犹新。至此,我写下来,教育青少年朋友们...
来源:清廉网作者:徐文惠2019-02-22 11:24
2016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我父亲王宏坤也参加了伟大而又艰苦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1935年的3月28日夜,为了实现...
来源:清廉网作者:王伟伟2019-02-22 11:14
201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来电人说自己江西省石城县楂树坪村村民,他们一直寻找当时六师的四个师级领导人:曹德清、徐策、杜中美...
来源:清廉网作者:欧阳晓光 刘无畏2019-02-22 10:42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无数坎坷,充满着传奇色彩。无论斗争多么残酷,任务多么艰巨复杂,他始终坚定信念、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后...
来源:清廉网作者:王小舟2019-02-22 10:25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的父亲黄克诚由于赋闲,偶尔也会和孩子们谈谈过去的事情,尤其是著名的红军长征。...
来源:《人民法治·清廉中国》杂志作者:黄 煦2019-01-28 16:28
经历了“文革”的劫难,父亲伍修权感到有必要让我们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于是在1975年春节第一次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革命历程。我们也是第一次聆听了他...
来源:《人民法治·清廉中国》杂志作者:伍连连2019-01-28 16:17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正值我们姨夫王稼祥诞辰110周年。我们满怀万分崇敬的心情,记述他在长征路上的一些故事。...
来源:《人民法治·清廉中国》杂志作者:谭国安 谭凯安2019-01-28 16:01
记得父亲在世时,常对我讲起这个故事。我的父亲王耀南1927年10月,跟随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他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创建了以宁...
来源:《人民法治·清廉中国》杂志作者:王太和2019-01-28 15:52
我的父亲谢觉哉说,1943年10月10日,艰苦的长征开始了。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战略意图是把红军主力拉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
来源:《人民法治·清廉中国》杂志作者:谢烈2019-01-28 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