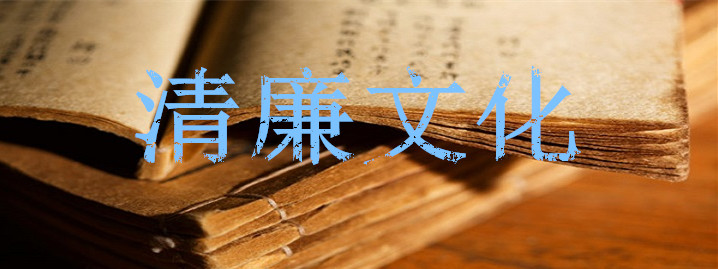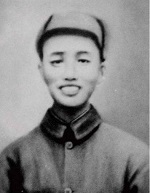道光皇帝节俭成僻
道光皇帝的节俭,受其父亲嘉庆皇帝的影响颇深。那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九月,身为太子的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祭奠先祖,晚上住在局促简陋的沈阳故宫。嘉庆皇帝特意命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糠灯、乌拉、拐杖等物品,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祖宗创业的艰难。道光会意,从此立志节俭律己。回京后,道光即与妻子约定过简朴生活,并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为省餐费,每日下午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因路远,烧饼买回来后,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连灯油钱都省了。
道光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库储备白银仅剩下2000 万两,而且虚账不少,非节俭不可。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带头节俭,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破了补补再穿,还规定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节庆日不得食肉,嫔妃平日不得使用妆容用品,不得穿锦绣衣服。道光还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内廷用款,每年不得超过20 万两银子,而前朝至少也要40 万两银子才能勉强支应。尽管皇后精打细算,但仍感入不敷出,于是,妃嫔们只好终年不添新衣,大家都穿破旧衣衫,连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
道光曾明确规定:停止举行万寿节(皇帝生日)、千秋节(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节)、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有一年,因皇后勤勉贤惠,道光帝决定为皇后生日祝寿,但招待满朝亲贵重臣的不过是一人一碗打卤面,大概可创国宴俭朴之最了。
道光对子女的教育,以节俭为基本立足点,曾作《慎德堂记》,告诫皇子皇孙们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应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至于儿女婚事,一概从简,总以不事奢华为度。
道光接待来拜见的外臣,免不了要宴请,但菜肴真称得上“寒酸”二字。有一年,大学士长龄平定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押送京师。道光帝亲御午门受俘,下令开庆功宴筵,为免浪费,特意传旨内膳房,须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人除长龄外,还有15 个老臣,挤了两桌,大家看着桌上可怜的几样菜,都不敢举箸,生怕一动筷就见底了,让道光皇帝面子上不好看。道光皇帝不吃菜也不喝酒,只顾高谈阔论,谈了足足两个时辰,大家一口菜未吃便散席了。
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爱节俭,下面的人是否也以节俭为美德呢?至少从道光一朝来看,并非如此。皇帝爱奢侈,下属是可以紧跟的,爱节俭就不行了,也许正应着那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道光帝拼命节省,下面的人却变着法子捞钱、花钱,结果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堵住两大漏洞。
第一大漏洞是内务府的虚报账单。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任何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价码立即翻着跟头往上涨。无论道光皇帝多么节省,银钱还是哗哗地流进内务府大臣们的腰包。道光皇帝虽然每餐只吃四个菜,照例总要花到800 两银子。后来他改吃素菜,不吃荤菜,每餐还是要花到六七十两银子,吃一个鸡蛋就要花五两银子,而按市价,五两银子买的鸡蛋够吃一年了。有一天,道光跟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闲谈,曹振镛说他每天早上要吃四个卤水鸡蛋。道光大吃一惊说:“每个鸡蛋五两银子,你一顿早餐岂不要花两银子吗?”曹振镛怕得罪内务府官员,赶紧奏称:“臣吃的鸡蛋,都是臣家中母鸡下的。”皇帝听了,笑道:“有这样便宜事,养几个母鸡,就可以吃不花钱的鸡蛋。”当下命内务府去买来母鸡,在宫中喂养,但内务府报销的每一只鸡要花24 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
据《春明梦录》载:有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时,道光看见他膝盖上打了个补丁,即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便说花了三钱银子,实际上,三钱银子差不多够买一条裤子了。谁知道光一听,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其丧尽天良,欺人太甚,打一块补丁竟然报销了上千两银子。谁知内务府大臣振振有词地说,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自然高,而且为了对上花纹,剪了几百匹湖绉,才补得天衣无缝,那价钱能低得了?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等费用也不低,总之一路算下来,好像一千两银子还算便宜的,全靠办事的人节俭才有此功。听得道光直翻白眼,无言以对。当下斥退内务府大臣,但打补丁的事以后再不交内务府干,就由后宫妃子代劳。但是,道光又是吃素,又是养鸡,又是让后宫打补丁,使内务府捞财的名目一个个减少,办事的人不乐意,就有点消极怠工了。据《春冰室野乘》载:有一次,道光皇帝想吃一种很普通的面食“片儿汤”,派太监跑去向御膳房要,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道光也就作罢,不再提此事。谁知内务府大臣又看上了这一捞钱名目,第二天早上,即奏请增设“片儿汤膳房”一所,经费为一万两白银。道光皇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须增设什么“片儿汤膳房”?但是,去买片儿汤的太监回来报告说,前门外饭馆有的已经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气得道光只有瞪眼的份儿。
总之,道光无论怎样节俭,钱还是没少花,一旦不能满足内务府大捞其钱的欲望,甚至连一碗片儿汤都吃不到。
第二大漏洞是官员的贪婪奢侈。道光崇尚节俭,而且特意奖赏懂得节俭的官员,企图在群臣中养成节俭的风气。据《清宣宗实录》载:有一次,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们都衣着朴素,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于是下旨,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既然节俭跟前程直接相关,官员们不得不在形式上效仿道光的做法,道光穿补丁衣裳,他们也穿补丁衣裳;道光在吃饭等花费上斤斤计较,他们也斤斤计较。官员们上朝时,往往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这么多补丁官员齐集一处,寒酸景象可真够瞧的。殊不知,那不过作秀而已。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有些穷官买不起旧衣,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再加上补丁。道光皇帝眼见满朝旧衣破袍,还以为自己倡导节俭起了效果呢!
尤为可笑的是,每日议事结束,官员彼此之间或互相哭穷,或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诸如此类。大学士曹振镛做得尤为彻底,力省每一个小钱,家中有一辆破旧的驴车,家里的厨子又兼赶车的差使,为了省一份工钱。
曹学士每天早朝回来,便脱去袍褂,从车厢里拿出菜筐秤杆,亲自买菜,和菜贩子讨价还价,常为了一文钱相互对骂。一旦争不过人家,曹学士就拿出学士凭证,要送菜贩子到步军衙门法办,菜贩子一看对方原来是朝廷高官,自然吓得屁滚尿流,急忙让价,曹学士占得一文钱便宜,便洋洋得意而去。道光皇帝听了他的趣闻,非但不讨厌,反倒如见知己,经常把曹学士召进宫去,谈得十分投机。
官员们的节俭,只是装给道光看的,私底下,该捞的钱一分不少捞,该花的钱一分不少花。例如,太后生日时,道光怕多花钱,下旨说,“天子以天下养,只须国泰民安,便足以尽颐养之道,皇太后节俭垂教,若于千秋大典过事铺张,反非所以顺慈圣之意”,因此大小臣子只须入宫行礼就行了,不送礼,不摆酒席。但相国穆彰阿表示,千秋节的一切开销都由臣民孝敬,不花内务府一文钱。道光一听挺高兴,同意了。结果,穆彰阿到各省大小衙门勒索孝敬,从一百两到五十万两银子不等,除极少一部分用于庆典外,足足捞了一千万两银子。
而官员们大发横财之外,挥霍成风,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生活极其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为了吃一盘猪脯,竟要杀数十头猪,有时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不断,声色犬马杂陈其间,可谓奢华备极,超过道光所享用的百倍、千倍。假设道光知道官员们是如此“节俭”,只怕会气得吐血,幸亏他什么也不知道。
一种好的风气,要靠良好的制度维持,仅凭领导的个人力量是行不通的。道光皇帝倡导节俭并没有错,但他过于依赖个人表现而非制度,非但无功,反倒养成了虚伪逢迎的风气,效果适得其反。
道光皇帝兴许是读多了古书。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自身行为不端,下属肯定不会乐于听命;但自身行为端正,下属也不一定听从。君子时常被小人诋毁、嘲笑,未必能被小人视为学习榜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确实像草一样,道德根基浅薄,风吹两边倒,但风过后,草还是故态复萌,哪会因风而发生“质变”?小人一时的随顺是可能的,但因君子而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是不太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轻制度、刑法而重道德、礼仪,是治道的一大弊端,贪官污吏本无道德可言,“礼”的约束力也很有限,必须用制度调整权益关系,用刑法增大“犯罪成本”,治贪才始见功效。如道光皇帝一味依赖“德治”,连身边的小人都治不了,哪治得了天下大贪?又哪能挽回大清日益衰竭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