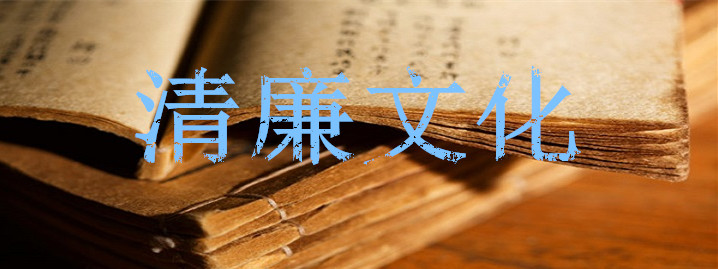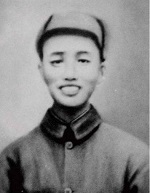朱元璋的廉政思想:严整吏治
朱元璋治吏之严酷,可谓历史上首屈一指。明初,朱元璋急于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可是任用的官吏“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他们凌暴盘剥,贪虐待民,徇私灭公,无所不为,直接影响和破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虽然朱元璋经常谕告百官,“导引为政,勿陷身家”,但是官吏们竟然无视上谕,“往往不依朕言”,照旧为非作歹,“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甚至连代表皇帝监察百官的御史也公然枉法,“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决心严整吏治。他说:“若不禁止,民何以堪!”“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严整吏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严密法网,以重刑严惩贪官污吏。朱元璋把元政之失,概括为“纵弛”二字,提出了治世用重典,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主张,并付诸实践。他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刑政者,救弊之药石也。”朱元璋以重典治贪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严峻,法网严密,二是法外用刑。朱元璋认为,唐宋以来,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例,胥吏易为奸弊,所以他在1369年命中书省定律令。他说,定律令“本欲除贪”,故不能“一事两端,可轻可重,使贪猾之吏得以因缘为奸”。可见朱元璋定律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贪奸和治贪奸。1371年,他下诏:“自今官吏有犯赃者,罪勿贷。”1385年10月,他颁布了《大诰》,之后不久,又颁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朱元璋在《大诰》序言中说:“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还接连颁布了大量的峻令。诸峻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当时律、例、令三者并行,不仅法网严密,而且立法严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条款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此外,朱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对贪奸之官吏施以酷刑。赵翼说:“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1385年,他规定:“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民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此外,还有捶楚、刖足、挑筋、去指、枭首、凌迟等重刑。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惩处贪官污吏最严厉、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当时,对贪官污吏,无论其官位高低,亲疏远近,一经发现,穷究不舍,严惩不贷。如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江浙富豪相勾结,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他便借此惩一儆百,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达“数万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破家的官吏、豪强更不计其数。
其二,治吏以惩戒教育为主。朱元璋说:“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育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戒二诰,颁不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刑用重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朱元璋以《大诰》为教材,“皆颁学官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对全社会进行普法教育。为了防范皂隶吏卒残害百姓,他还对吏员的家眷进行劝谕。他说:“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薄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总之,朱元璋以“重典”作为手段,“取决一时,非以为则”。目的是使全国臣民畏法、守法,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
其三,鼓励民众赴京告奸。朱元璋在《大诰》里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民众可以“连名赴京状奏”,持诰赴京,甚至可以将害民之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持诰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拦,即使没有“文引”,也要放行。否则,官吏“族诛”。朱元璋试图借助民众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这样的规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许民持诰赴京告奸,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民众拥有制约官府的权利,并给予这种权利以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朱元璋许民告奸的前提是皇权的绝对权威,强调皇权对民众利益的庇护,其实质仍然是由君主制约臣民,而不是民众自身权利的体现,说到底不过是比较高明的治吏术而已。
由于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使明初的吏治比元末有所改进。《明史·循吏传序》中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此话虽不免有夸大之词,但吏治有所澄清,则确实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