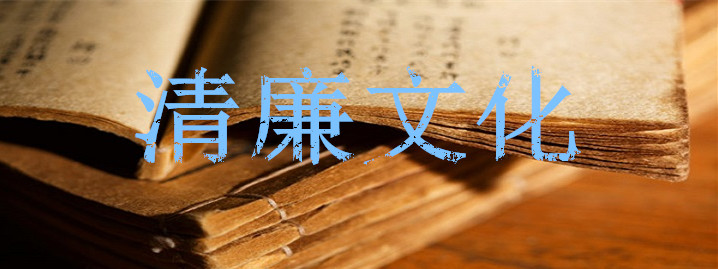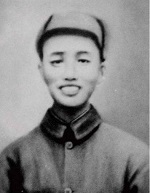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飞虎将军”肖全夫(二)

四、痛击“王牌师”
1953年6月18日,朝鲜停战前夕,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好战分子的怂恿下,假借“就地释放”之名,强行扣留中朝战俘,严重地破坏了已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并公开叫嚷“反对朝鲜停战”,要“单独干”和“北进”,妄图破坏朝鲜停战的实现。
几天以后,志愿军首长在接到毛泽东主席同意推迟停战签字时间的复电后,立即向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在全线发起第3次反击的命令。
“好呀,一三六师攻打马踏里东山的作战方案中旬就报来了,曹海炳参谋长几次打电话催我批准他们的方案,因为当时正在停战谈判,我把它压下来了。现在敌人反倒找上了门,不再狠狠地教训他一下,就不会有真正的停战。”接到命令后,时任志愿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的肖全夫高兴地说。
他请示兵团后,即令一三六师抓紧战斗准备。
马踏里东山由4个高地(编号:060、061、062、+0238)组成,是敌人从纵深经过临津江渡口,通向其右翼的阵地障屏交通。其西、北两面距我防御阵地仅二三百米,其东、南两面均有公路和小平川与敌右翼及纵深阵地相隔,是敌前沿阵地较孤立的重要支撑点。该地有坑道3条,大小地堡157个,明暗火力点90余个,堡、点间均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其外围有各种形状的铁丝网三至四道,前沿设有防步兵地雷和照明雷等,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完整的环形防御阵地。
防守该高地的为敌土耳其旅一个加强连,061、062高地为其前哨阵地,各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防守;060,+0238高地为其主阵地,由连主力守备。
正当一三六师积极准备攻打马踏里东山时,敌情发生了变化:土耳其旅撤下去了,美陆一师换上来了。
土耳其旅,这个曾经在世界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后裔、狂热的宗教徒,本来就有很强的战斗力,它是派遣到朝鲜战场上的外国军队中仅次于美军的劲旅。而在这个节骨跟上,却把防务交给美陆一师,显然是敌人想在停战前夕利用这张王牌守住每一寸土地,甚至最好能抢回一点地盘。因为,这个时候,丢失的阵地将会成为对方永久性的领土。
美陆一师,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据说有175年的建军史,曾4次出国作战,号称“打遍地球无敌手”的王牌师。1950年,当美国派遣该师到朝鲜战场上来时,其宣传机构曾这样吹嘘道:“这些军队有着典型的美国军队最好的品质,他们的装备是在朝鲜战争中所见到的最好的。如果共军能打败这一伙人,那么他们就已经赢得了朝鲜的战争,甚至是全世界的战争,因为这一伙人是我们军队中最精锐和最优秀的。这些海军陆战队承认他们也许有一天会被打败——是的,如果那一天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话。”
“骨头越硬,啃起来越有味道!”肖全夫说。
为了打好这最后的“压台戏”,他带着电台去前沿一带查看地形。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左看看、右看看,看看哪儿有个大石头、哪儿有个沟坎,各个方位物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对此,他解释说:“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最主要的是搞清地形,因为敌情是可变的,而地形是不变的,只有搞清了地形,才能决定投入多大的兵力、火力,突击点选在哪里,怎样才能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一举歼灭敌人。”
整整看了一天地形,肖全夫心中有了腹案,天黑后才赶往一三六师,和师、团干部一起研究攻打马踏里东山的具体方案。
按照他的部署,7月7日夜里,四○七团一连在43门火炮支援下分4路向062高地发起攻击。经过3个半小时的激战,摧毁田堡6座,地堡70余个,坑道两条。至8日2时攻占062高地,全歼守敌。接着击退敌7次冲击。战至黄昏,歼敌300余人,俘敌3人,查明了情况,遂按原计划撤出阵地。
一打马踏里,顿挫了敌人的猖撅气焰。9日,美方谈判代表几次找上门来要求恢复谈判。中方代表团负责同志在决定恢复接触时,对肖全夫作为该军代表派往谈判的一三六师胡旭副参谋长说:“你们的炮声震动了板门店,你们打痛了敌人,我们就又有事可做了。”10日,美陆一师参谋长迫不及待地在谈判桌上发言:“各位先生,为了节约大量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先把西部军事分界线固定下来。”
敌人已经预感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一天就要到了。
13日,志愿军在东线展开了大规模的金城反击战。为配合这次作战,肖全夫又一次来到一三六师,部署第二次攻打马踏里东山的战斗。按照计划,这次不仅要夺占两个前沿高地,而且要坚决固守。
19日夜,我四○七团两个连在61门火炮支援下,向062、061高地同时发起了攻击。由于战前准备充分,仅40余分钟即攻占敌阵地,全歼守敌。转入守备后,敌以80余门火炮、19架次飞机支援其步兵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冲击,企图夺回阵地。至21日夜,坚守分队共打退敌5个多连兵力的17次反扑,毙、伤敌人507人,俘敌12人,守住了已得阵地。
二打马踏里一结束,胡旭便告诉在谈判桌上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的那个美陆一师参谋长:“上校,马踏里战线已经南移了。”气急败坏的这位上校竟大声吼道:“我们陆一师的防御正面,寸土未失!”说完便溜回自己的帐篷,大喊大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
显然,这是为了“保全面子”说给外国记者听的。那位美陆一师参谋长很清楚,他们丢失的阵地并非没有去夺,而是对手太强了。中国人要固守的阵地是一个填不满尸体的无底洞,要夺它,除了继续延长那已经够长的死亡名单之外,别无他法。
24日,肖全夫命令部队向马踏里东山最后两个主阵地发动第三次攻击,一举夺占060阵地。敌人不惜血本,拼死反扑,均击退。正当部队向最后一个高地+0238攻击,并已占领整个阵的四分之三时,停战令生效了。
三打马踏里战斗,前推阵地1平方公里,歼敌1643名,俘敌21名,毁伤坦克7辆,缴获各种枪支157支(挺),子弹30余万发,狠狠地教训了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师”,直接配合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和东线的进攻作战,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板门店前线的“收官之战”。
五、捍卫珍宝岛
1969年2月,在东北中苏边界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全夫受军区党委之托,将苏军对我进行武装挑衅的情况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中央军委,并直接到北京向中央请缨。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听取了他的汇报。
温玉成问:“如果反击,你们准备选择在什么地段?”
“珍宝岛。”肖全夫答道,“目前,我们边防站兵力单薄,除了已经把各军的侦察连调上去以外,还准备动用一些部队作为二线的预备队。我们立足于小打,也防备他狗急跳墙。”
温玉成说:“你们呈送军委的报告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有关情况也直接向总理和主席做了汇报。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对苏修的武装挑衅,要坚决予以反击。只不过,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即这是一场局部的边界冲突!”
3月2日,苏军在珍宝岛悍然开枪袭击我边防站长孙玉国带领的巡逻队,早已严阵以待的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战历时90分钟,我军牺牲20人,苏军战亡40余人、伤30余人,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篷卡车各1辆。当日,沈阳军区决定在前沿设立虎(林)饶(河)前指,由肖全夫和军区李少元副政委负责统一指挥。
肖全夫的前指设在离珍宝岛不足10公里的五林洞。他调动1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通信连、18个炮连、侦察连和机枪连,并将23军67师作为战役预备队进驻牡丹江市。周总理在北京问前来参加党的九大筹备工作的陈锡联,“谁是前线指挥员?”听说是肖全夫时,总理笑着说:“这回,苏军可是遇到对手了。”见陈锡联有些疑惑不解,周总理解释说:“我记得,这个肖全夫曾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那里的教官都是苏联人,对苏军的那一套,肖全夫清楚得很!”
3月13日,苏军3辆坦克开进我方境内。肖全夫立即向陈锡联和温玉成汇报,并采用一个万全之策,命令部队用迫击炮轰上几炮,将苏军坦克赶走了事。这样才使我军的火力配置和战斗意图不至于暴露,从而保证了在随后3月15日的几次大的战斗中达到预期效果,击毁苏军坦克4辆、装甲车7辆,击伤坦克和装甲车4辆,毙伤苏军170多人,其中苏军上校和中校指挥官各一名。周总理听到战果汇报后,称赞说:“这个肖全夫,打得不错嘛!”
六、天山筑“铜墙”
1980年1月,肖全夫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他深知新疆在祖国统一大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深感自己的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到任后,他牢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托,以维护新疆的稳定与统一为统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贯彻军委“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预案。
1982年,他亲自筹划并组织了“三战”演习(游击战、运动战和坚固阵地防御战)。总参谋长杨得志参观演习后说:“它不仅是乌鲁木齐军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也是训练改革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新疆部队的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和后勤建设,都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对于全军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第二年,他又组织了有党政军民参加的陆空协同反空袭、反空降演习,对提高各军兵种战术技术水平、增强全民防空意识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他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的指示,结合新疆部队的实际,提出了“军人要像个军人的样子,营区要像个营区的样子,部队要像部队的样子”的具体要求,加强部队的军容风纪和作风纪律整顿。同时,他还在全区部队普遍组织了阅兵式、分列式的演练,他决心在天山筑起保卫祖国安全的“铜墙铁壁”。
乌鲁木齐军区部队守卫着6700多公里的边防线。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数边防部队驻守条件非常艰苦,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很差。肖全夫看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几次到北京向军委反映边防官兵的困难和疾苦。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总后勤部给乌鲁木齐军区拨出专款,用于边防设施建设。对此,肖全夫亲自进行动员部署,提出了搞好边防建设的“八好”要求和具体标准,并多次到工地检查施工。1984年8月,在他68岁高龄时,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到素有“永冻层”、“生命禁区”之称的阿里防区和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视察。在此期间,他强忍着严重的高山反应,看望守防和施工部队的官兵、检查边防建设情况。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新疆几万名边防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肖全夫一贯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80年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军营,部队中思想比较活跃。为做好转型时期官兵的思想工作,他与政委谭友林一起狠抓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亲自上党课、讲传统,教育大家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他要求部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肖全夫常说,新疆是多民族集居地,只有搞好军政军民和民族团结,才能维护新疆的政治稳定。作为自治区区委常委,他自觉服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并积极参加区委的集体活动,对新疆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动员等工作发表重要意见。为加强民族团结,他主动同少数民族干部交朋友,并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学习体会,提出“深入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妥善处理民族纠纷、积极主动地为驻地少数民族做好事、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工作思路。他亲自参加部队组织的打扫积雪、植树造林等助民劳动;亲自到吐鲁番市考察,指导军地双方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新疆“双拥”工作的深入开展。
(彭德怀与肖全夫在前沿阵地上)
肖全夫始终把承担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作为部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当辽河决口和营口、海城、乌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他每次都率领或指挥官兵及时赶到灾区,精心组织抢救。1970年,为解决全国性动力燃料告急的被动局面,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修建从大庆通往抚顺等炼油厂的输油管道,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肖司令员被任命为输油管道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为按时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团结和带领地方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民工、战士,克服重重困难,苦干五年,修建了8条输油管道,总长达2400多公里,开创了我国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的先河。
肖全夫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修身砺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对事业忠贞不渝。“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威逼他交待“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他坚强不屈,没有讲一句违心的话。最后一次病重住院不久,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写下遗嘱:在我去世以后,从我的积蓄中拿出5万元,其中2万元交给党组织,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3万元捐给家乡的希望工程,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比热爱和赤胆忠心。
他一生勤奋好学。参军前,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在南京学习时,他经常学到半夜从教室回家,还叫醒夫人帮他复习,毕业时被评为“模范学员”。他经常学习到深夜,并将学习《邓小平文选》《朱德文选》的体会撰文发表,指导部队的学习和实践。1985年他退居二线后,仍然自觉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香港、澳门、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他不顾体弱多病,经常深入各地调研,写出调查报告和文章,提供给有关领导参考或在报刊上发表;还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
他善于团结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在军区工作期间,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他不仅注重加强军区党委班子的内部团结,还十分重视抓好部队各级班子的团结协作。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整编后的新疆军区隶属兰州军区。他与常委们一道多次召开会议,对军区机关、部队官兵进行顾大局、守纪律、正确对待升降并改和进退去留教育,保证了军区的稳定和精简整编任务的顺利完成。
他虽身居高职、手中有权,但他一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1983年,他的搭档、政委谭友林调出任职,新任政委谭善和到任。为了表示对新老政委的迎送,他提议军区党委常委每人掏出5元钱,共进一餐。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不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办事。他经常教育子女们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凭本事而不是靠“老子”吃饭。他在生前就对自己的后事留下嘱咐:“丧事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