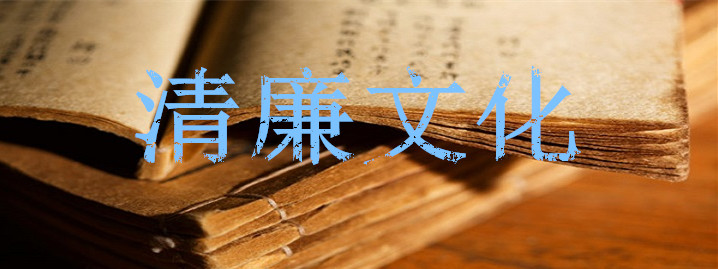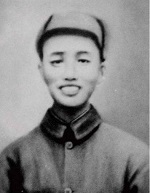江春霖:铁面御史 廉善传家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洋山人,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梅洋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名列第一。历官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不久,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擢监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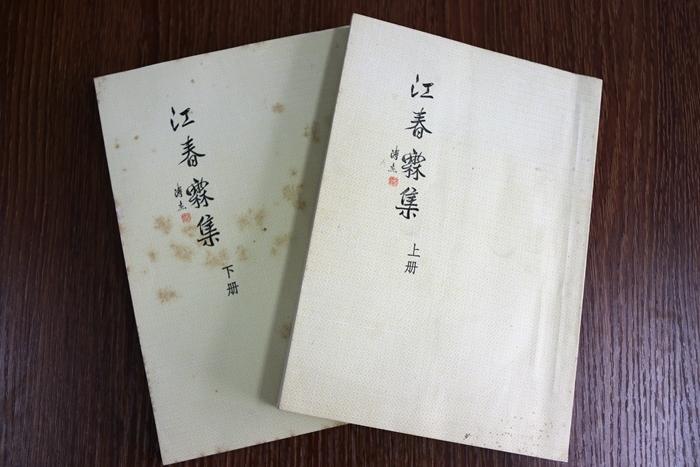
江春霖从小就熟读经史,敬仰诸葛亮、包公和海瑞的公正廉洁,立志:“我志在四方,如果不当谏官,怎么能实现我的抱负呢?”
清朝末年,权臣营私舞弊,祸害百姓。他不顾自身安危,五任御史,先后上疏68件,评议时政,弹劾权臣污吏。从庆亲王奕劻父子、军机大臣直到都御史,被他指名道姓的就有15人。其中,专摺严劾袁世凯“交通亲贵、把持台谏”等十二条罪状,朝野震动。因而被誉为“古今第一御史”,“光绪、宣统以来谏官第一人”。1910年2月再参奕劻,触怒朝廷而被罢职。江春霖以其大无畏、独立特行、为民请命的精神,敢于批龙鳞,捋虎须,实现了他作为监察官“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行于奏牍”“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的志向。

“雪貌冰姿冷不侵,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这是江春霖表明心迹的自白诗《咏水仙花》。江春霖虽早丧偶,仍不续娶,即使一涉贪官员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连夜上门送给他做续弦,也被他愤然斥责轰走;在朝为官十分的自律,一直秉持三不原则:一不添置田产,二不兴盖房屋,三不蓄养奴婢;为官期间,把母亲、夫人和弟弟全家留在老家,过着十分清贫艰苦的农村生活;自己亦生活俭朴,自理炊事,常以笋干佐饭。辞官出京之日,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筐而已。全御史台知其贫而廉,大家凑集二千两银子为他送行,以表临别敬意,江春霖却以诗婉辞不受,诗中“俸余只剩卖书钱”是其十几京官、两袖清风的真实写照!

江春霖回莆田时,县城人士超过万人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时莆田县令说:“自从明朝黄仲昭因直谏朝廷耽于逸乐、粉饰太平,触怒了宪宗朱见深被廷杖回到莆田时,莆田人曾在这里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之后,五百年过去,此种盛况今天再次见到”,“足以代表真正民意”。

回到莆田的江春霖在关心民众疾苦的同时致力发展地方公益事业。1914年,江春霖主持兴修梧塘沟尾海堤(今涵江韩坝),还捐出长期积累的5000枚铜板救灾,7万亩良田受益。此外,他还募修涵江南埕、镇前海堤及哆头“乌菜港”等陡门,以及兴仁医院(今涵江医院)、湄洲天后宫等公共设施。同治年间,江春霖父亲江莲溪修建的萩芦溪大桥被冲毁后,临终前,嘱咐儿子江春霖二兄弟一定要在萩芦溪上再造一座桥。随后,江春霖、其弟江春澍和几个子女“接力”重建萩芦溪大桥。6年后,萩芦溪大桥终于建成,方便了南北交通。如今桥上有座“御史亭”,就是群众为纪念江春霖而建的。

家风,是一个家族灵魂的延续。江春霖从小耳濡目染莆阳江氏家族“明礼让、笃宗盟、厚亲戚、勤耕绩、恤孤寡、禁砍萌、慎嫁娶、止赌博、禁游惰,息争讼”传统家风,并在这种优良家风熏陶下成长。
走进“百廿间大厝”江春霖祖屋,一幅“积善不忘祖宗训,遗书独望子孙贤”的对联格外醒目。江家大厝的顶厅,至今似乎还回荡着江御史的谆谆教导之声:“民穷财尽,子孙即能继起,须教以廉节,力戒奢华……”他给其四子的信中云:“……为问到贫无所措时,能不俭耶?能更奢耶?”翻开《江春霖文集》,家风家训类的诗文随处可见。光绪乙未年(1895),江春霖将“新厝里”改造为“二层楼房”,以方便后代读书。为此,他命其名为“半耕书室”,并专为该书室写一篇跋——半耕书室自跋。跋中“示子孙毋忘稼穑艰难也”等箴言,倡导后世子孙要“入为肖子,出为良臣”,激励江氏后人崇德向善,兴家报国。

民国3年(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因江春霖修建莆田水利有功,请授以四等嘉禾勋章,被他拒绝了。民国七年,江春霖病逝,终年63岁。邑人史学家朱维干教授有云:“吾莆受治爱新觉罗氏,二百六十七年中,堪称为完人者,(江)侍御一人而已!”(莆田市涵江区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