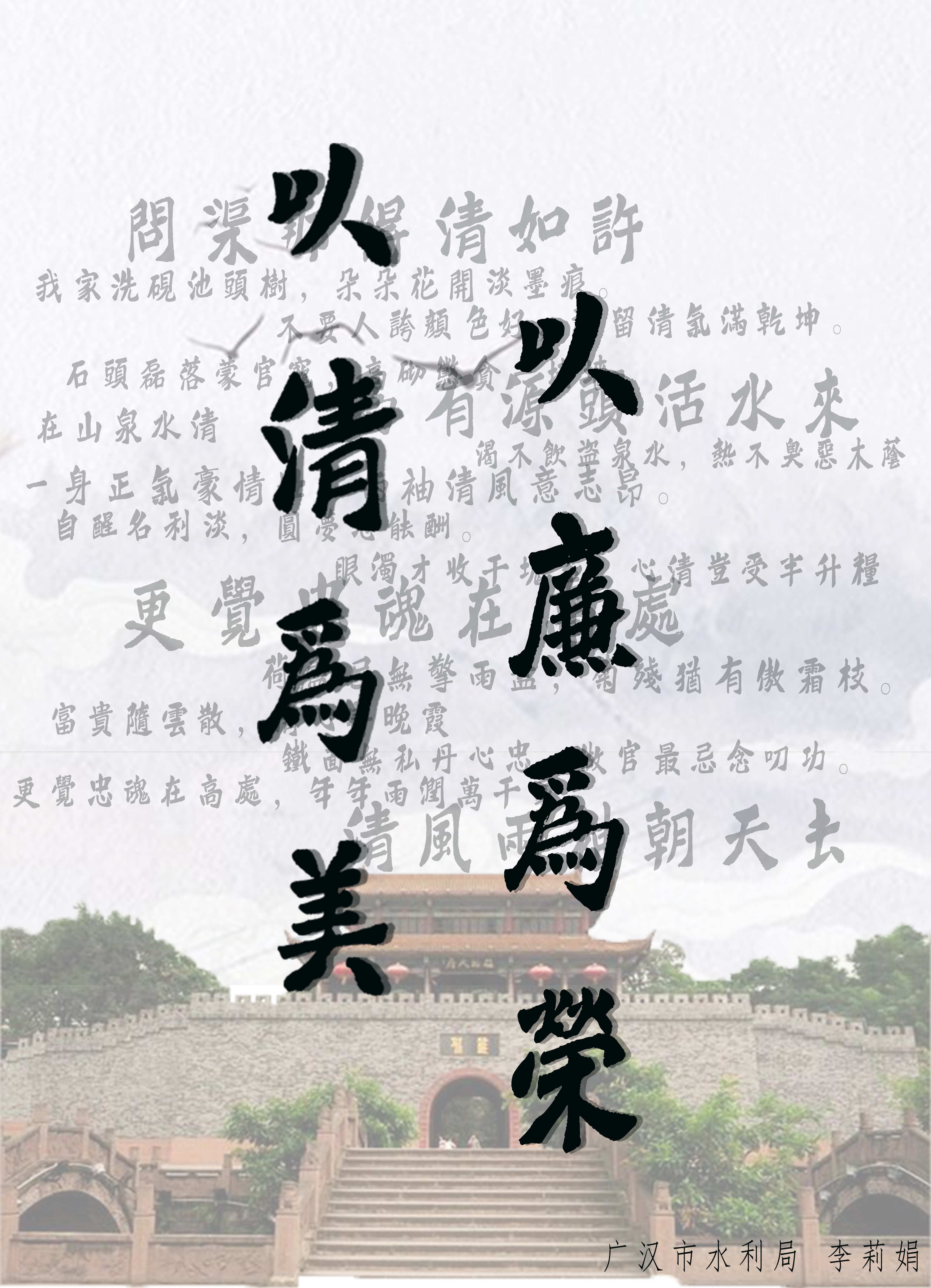唐代的温卷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自己的诗文)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唐代以科举取士,考卷都不糊名,应试者事先可以将自己的诗文送呈政界要人或文坛名宿,请求推荐,因而凡是有进取心的士子,无不干谒,以求当路之知。
对于“诗圣”杜甫“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其实,杜甫是功名欲望很强的人,“学而优则仕”的三种门径——科举、温卷和向皇帝陈情,他都闯过,而且不止一次。杜甫曾参加两次科举,但都名落孙山。杜甫曾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750年)进献《雕赋》;第二次是天宝十年(751年)献上《三大礼赋》;第三次是天宝十三年(754年)呈上《封西岳赋》。除第二次受玄宗“奇视”而命待集贤院外,杜甫均未得到垂青。至于恳求权贵的荐举,那就更加频繁了。《杜工部集》收有不少天宝年间行卷之作:《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翰林张四学士垍》、《上韦左相二十韵》……无论是向皇上陈情,还是恳求权贵汲引,杜甫都要赞美皇帝,吹捧权贵,继而哭穷。因而王夫之指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但是,潘德舆认为:“(杜)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
“诗仙”李白也有许多干禄之作。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刚从巴蜀至长安的时候,住在旅店里。秘书监贺知章听说他的名声,第一个探访之,觉得他容貌非凡。李白拿出《蜀道难》给他看,贺知章还没读完,就连连称赞,称其为“谪仙”,解下金龟(官员的腰带)换酒,与李白喝得酩酊大醉,一连这样好几天, 于是李白的名声逐渐显赫。后来,李白被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作了翰林学士。
再说素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的白居易,“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只在人间活了二十七岁的“诗鬼”李贺也曾见知于道德文章名重一时的韩愈。“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剧谈录》)
通过行卷求仕,这在唐代文士中并不鲜见。有的说得直露,譬如李白《与韩荆州书》:“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有的人说得含蓄,譬如孟浩然。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为相,孟浩然曾去相府行卷:“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临洞庭上张丞相》诗,前四句写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气势,后四句意思是说,想渡湖而苦于没有船只,想做官而苦于没有援引,生当盛世而无所作为是感到可耻的。我看到渔夫钓到了鱼,内心羡慕不已,可我没有垂钓的工具。言外之意,我空有做官的愿望,却难得有一个荐举自己从政的人。张九龄也善写诗,自然明白孟诗的真意。遗憾的是,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对孟浩然爱莫能助。孟浩然应试不第,又还故里襄阳。后张九龄被贬,出镇荆州,曾招之于幕府,但是二人共事只有四年时间就先后病故了。
还有一种温卷的方式是效法《楚辞》,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社会关系;用借此喻彼的手法来表达希望人家荐引的意思。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朱庆馀的《闺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又题为《近试上张水部》。诗是写给水部郎中张籍的。张籍极善写诗,与韩愈齐名,而且乐于提拔后进。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还怕自己的作品不符合主考的要求,因而以新娘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比主考,写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有趣的是,张籍在收到朱庆馀的《闺意》以后竟也用同样的手法写了首答诗,题为《酬朱庆馀》,诗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张籍索性就把他比作一位采菱越女,新样靓妆,出现在镜湖的湖心,她明知自己长得很美,光彩照人,可是因为求强好胜的心太迫切了,她反而忐忑沉吟起来。越女过于想打扮好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疑惑不定,倒要去问人家这个样子是不是好看。接着,张籍进一步肯定朱庆馀才艺超群,齐地(今山东淄博)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并不值得人们看重,而是那明艳越女的“一曲菱歌”,才是真正可以“敌万金”的呢。实际上是张籍暗示朱庆馀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后来,朱庆馀果然金榜题名,官至秘书省校书郎。
诚然,对有才能的后辈,给以延誉以至奖掖,使他们能“出人头地”,发挥其所长,并非坏事。但是这种温卷之风往往又给那些“跑官”者大开方便之门,难免鱼龙混杂。章碣有首《东都望幸》,诗云:“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显然,这是一首宫怨诗。唐以洛阳为东都。诗咏在洛阳的宫女盼望皇帝巡幸洛阳,以期承恩受宠,但是终究落空的懊恼心情。她已懒于将自己打扮得翠绕珠围,登上高台去望君王车驾的来临了,就像新月弯弯一般美丽的双眉含颦深蹙,难得展开。为什么呢?因为身在东都,不比长安的宫女,可以有较多的机会接近皇帝。纵然皇帝东巡,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会把长安的美女也带了来,这样,自己又怎么可能获得恩宠呢?这真是绝望了。但据《唐摭言》记载,这首诗是章碣写来讽刺高湘的。高湘从南方回长安,路过连江。邵安石将自己的诗作呈献给他,颇受赏识。他就将邵安石带到长安。后来他以礼部侍郎主持进士考试,邵安石就及第了。由此可见,温卷也有弊端,同时也反映了小农社会人才的总需求量不大的现状。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杂说》)这不仅是韩愈的人才观,也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信奉的一种人才观。换句话说,人才是有的,而善于发现或培养人才的人不常有。因此,即或是一匹千里马,要是遇不上伯乐的话,也只能“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韩愈《杂说》)。“千里马”要脱颖而出,理应主动去追“伯乐”,这就是唐人温卷的内在逻辑,也可以说是后世“跑官”之风漫延不绝的文化根源。有所不同的是,唐人温卷还要借诗词歌赋来炫耀才学,展示抱负,说来多少还有些含蓄,有些文化味,而后世那些“跑官”之人,靠得却是财货美色,一旦掌权就要追求“回报”,攫取更大的权力和私利。其实,“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旦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不但“千里马”不再有,就是“伯乐”也不再有了。(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