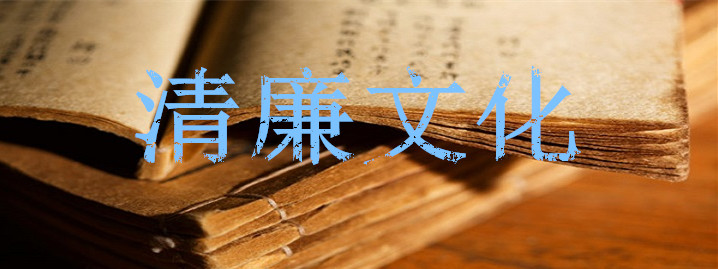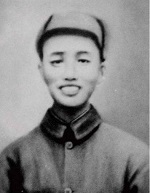康熙引进夜来香
以前,我一直以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又名夜来香),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徐珂的《清稗类钞》,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锡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
玄烨在位的六十一年,是大清朝的鼎盛时期。虽然其执政晚年,吏治松弛,纲纪紊乱,出多入少,以致国力大降,害得儿子雍正继位时国库空虚,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晚年的康熙比起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还算差强人意。虽然有点昏庸糊涂,但还没有倒行逆施;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还没有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从夜来香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看,一枝来自外邦的花,康熙准许在禁苑中种植,并为之命名,说明这位皇帝不顽守故旧,不拘泥陈习,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展开胸怀,拥抱世界。据说,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将西方音乐献演于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乐在中国的首次演奏,当乐声飘扬在整个紫禁城时,对持夷夏之别的人士来说,该是多么骇人听闻了。然而,在御座上的康熙却听得很在意,很入神,这自是他不小气、不狭隘、不封闭、不排外的精神气象了。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一个大国应该具有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等物品,都是在汉代引进中原,从而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会表现出一种坦然、大度、自信、开放的精神状态。
我始终弄不懂,康熙敢在御花园里种“土必盈斯”,接受外来事物,可康熙后代的后代,怎么就被列强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
清末,有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便是畏外拒外的愚昧典型了。他支持义和团,就因其宗旨是扶清灭洋。他甚至说,洋人为何走路笔直,因为他们的腿不会打弯,所以,只要发给兵勇们一根木棍,将洋人拨倒在地,他们就无法再站立起来。这成为一时笑谈。戊戌变法后,慈禧讨厌光绪不听话,立溥俊为大阿哥,聘徐桐为师,因此每天要进宫教习。可他家住在京师崇文门附近,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当下的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不忍目睹的。可他不仅是大阿哥溥俊的座师,要言传身教,还是老佛爷和满朝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柱石,不能不克尽厥职,每天必须进宫。因此,他让轿夫们,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风景。这位年过八旬的徐大学士,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这就是清代末季道、咸、同、光江河日下、国势衰颓的写照。一朝比一朝不成气候,精神上畏葸退缩,行为上闭关自守,思想上顽固保守,恐外排外、惧洋畏洋,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玄烨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史称其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天文历法、舆地测量,无一不下功夫钻研。有一次太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奶奶诊病,毫无戒备防范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信心百倍,才能宽容;力量十足,才能大度;胸怀辽阔,才能厚德载物;精神进取,才能登高望远。从夜来香引进中国的来历,便觉得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多么高明的识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