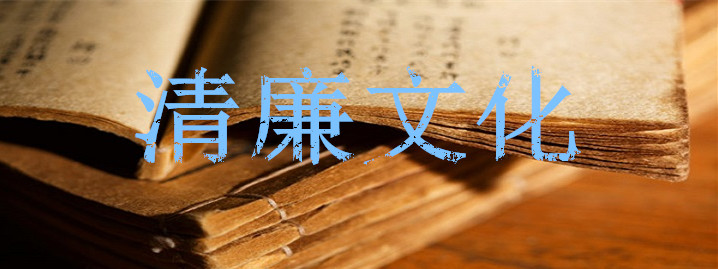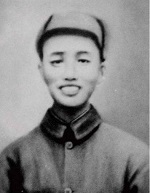“以心会心”求圣贤之道
戴震(公元1723―1777年),安徽休宁人,乾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与考据学家。青年的戴震,基本上靠自学成材。35岁后,与社会贤达、名流、学界精英广泛交往,学术与哲学思想变得更加丰满与圆通。其治学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试图通过文字、训诂、古代制度史、科技史的人文学的实证方法,来探求儒家经文中蕴涵的深邃哲学之道。有学者将此方法统称之为语言学的解释学方法。我个人将其称为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二是在坚实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的基础上,要求研究者扩大自己的心量,去领悟古圣贤与天地之心相协的广阔心胸,从而把握儒家经文中深邃的哲学意蕴。通观其一生的治学方法,我尝试将戴震的治学方法概括为:科学的实证精神与哲学的会通精神相统一的方法。
在《与是仲明论学书》这封书信中,戴震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他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他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运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戴震属于自学成材型的学者,他家里贫寒,无力延请老师,完全靠自己去钻研儒家的经文意思。他领悟到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语言学的方法。而“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包含了现代解释学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的循环方法。在该文中,戴震还从更加广阔的文化史角度,即“知识考古”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经典的原意。他说,要读懂经典除了识字、断句,通过语言来理解经文中的思想之外,还需要懂得古代天文学、音韵学原理、宫室建筑体制、礼制制度史,要懂得古代地理知识,包括江河名称的变化与流经位置的变化,要懂得古代的技术与工艺知识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懂得鸟兽虫鱼草木的性状、分类与名称,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尚书》、《诗经》,也才能理解礼制方面的书籍,从而真正全方位地把握儒家经文的意思。
上述戴震所提出的方法虽然局限于儒家经文研究,但具有广泛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在其中年与晚年的著作《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中,又细化了其语言学方法,通过句法的分析来重新解释儒家经文的意义,颇具新意。
戴震的治学方法之所以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而不是科学的实证主义,还在于他对儒家经文的解释,并不是完全依赖文字、语言、古代典章制度等实证性的知识来实现的。中晚年的戴震也强调研究者要扩充自己的心量,从而去理解古代圣贤协于天地之心的广阔心量,进而去会通儒家经文中的深邃意义。此一治学方法,在近百年的戴震研究者中很少有人关注。在《古经解钩沉序》一文中,他一方面强调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戴震的意思是说,古代的“道”并非简单地指客观的法则,其实也是古代圣贤与天地根本精神相契合的一种心志,并将这种心志与民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并满足民众的愿望,这就是“道”。
所以,他在《郑学斋记》中又说道:“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
研究儒家经文的人要做到自己的心与古代圣贤的心志相一致,这样才能通过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研究,由语言的途径上达对古人之道的理解。他甚至还说:“读《春秋》者,非大其心无以见夫道之大,非精其心无以察夫义之精。”这样,通过“深求语言之间”以及古代制度史、科技史的人文实证科学方法而能自造新意,又以我之“精心”逆遇古圣人之精义的正确创新途径,实现对古代经文的正确理解,进而能实现思想的创新。
强调研究者之“精心”在言与道之间发挥作用,正是戴震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在追求经典解释的客观性时,力求避免机械论、客观反映论之类的简单化认识的要义之所在,也是他力图使考据学避免走向纯粹的文人智力游戏的理论意图之所在。戴震所提倡的这种“以心会心”的“哲学会通”方法,由于有人文实证方法为底线,不至于流入主观的臆想之中,而更多地会展示其创造性,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典范的例证。因此,戴震的“以我之精心来逆遇古人之精义”的方法其实就是戴震创造的哲学解释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