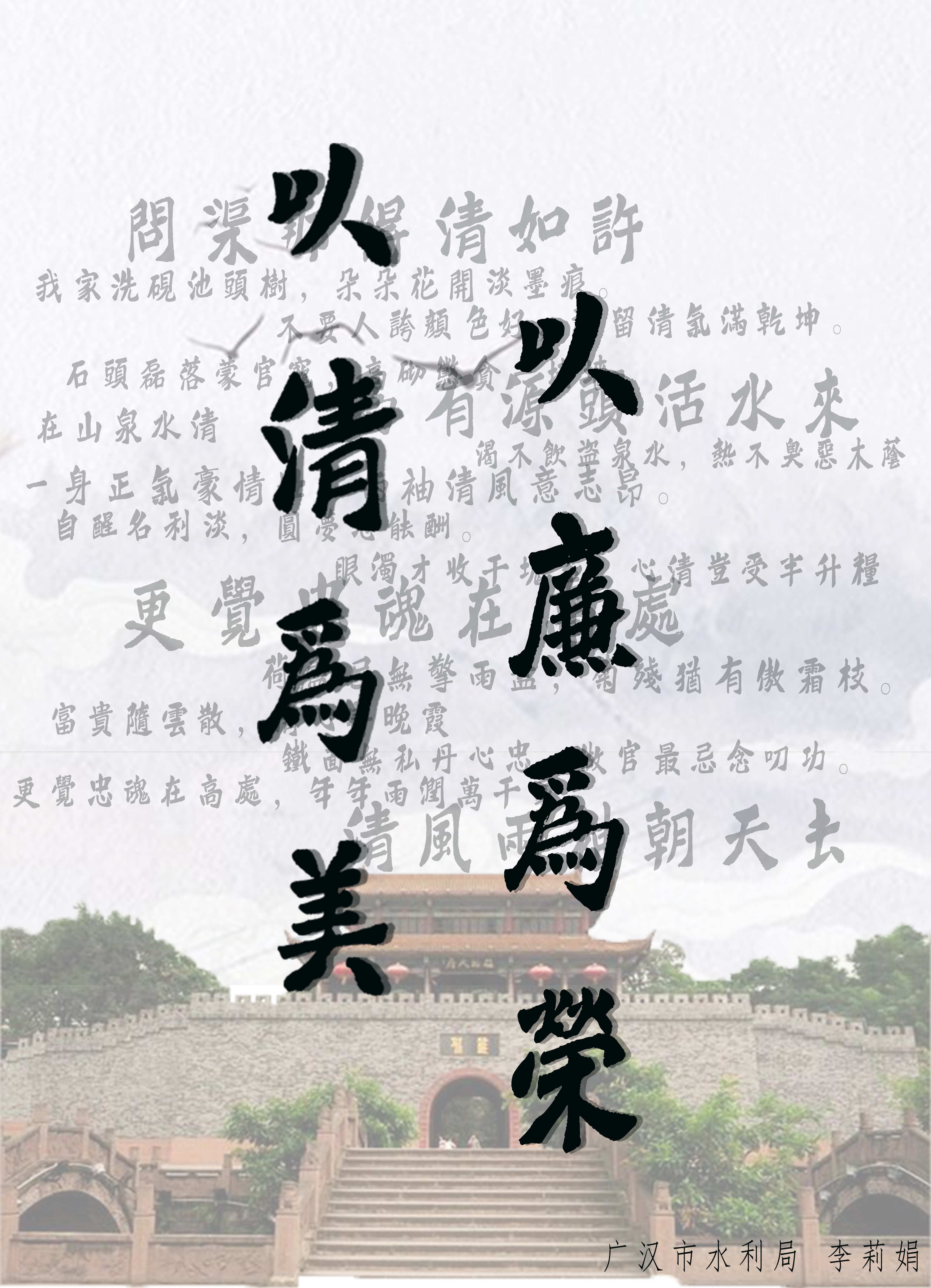怀念父亲
32年前的一天,天蒙蒙亮,我和父亲上路了。
秋风带着宜人的凉爽,将田野的稻香味儿吹来。我沉默无语,父亲也低头走路不说话。这么走了半晌,父亲咳嗽了两声,开腔道:“学农业好,将来有饭吃!”我的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稻田,几只叫不出名的雀儿振翅飞翔,欢快如同孩童般。见我不说话,父亲又说:“农业稳当,靠得住!”
昨晚,我把高考录取通知书扔在地上,发誓不去上中专。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怎么考的呢?强项没能发挥出水平来,反倒平时一般的功课出乎意料地让人满意。“你可以选择复读,明年上大学没问题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都这么劝导。我在矛盾中过了一天又一天。通知书下发时,我的泪珠儿真是一串串往下流。其实,我是别无选择的。只得上路,却心如枯井,语言的泉水被蒸发了。
从戴圩到夏集,五华里的路程,我一言未发。
父亲买了几根油条,一张油腻的报纸包着,散发着热气。“垫垫肚子,还有老远的路呢。”父亲递给我一根油条,一双青筋突暴的手,缀满了老年斑。我的心尖颤动一下。“不要送了,我自己走就行了。”我说。若是再复习一年,父亲的手又该会怎么样的苍老?家里人又该多么提心吊胆?17岁的少年,仿佛明晓了事理。“再走走吧。”父亲依旧坚持。我的心情开朗了许多,开始讲话了。我告诉父亲,自己高考前高烧,考试时竟然迷迷糊糊打起瞌睡。或许此生与大学无缘,一辈子注定要搞农业了。父亲重复着刚才的话:“学农业好,稳当!”我鼻子突然发酸。父亲年轻时做过官员,十年后,举家返乡做了农民。或许因为对官场存在某种恐惧,他反复劝慰我的词语,竟只有这几句。
一路无语。到了小镇濠城。父亲交代一番,送我上了公共汽车,才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
26年前的那天,我回到村庄,站在老屋前,呼吸村野暮色中牛粪野草炊烟的混合味儿,心绪随淡淡雾霭,氤氲开来。一轮太阳燃烧在无尽的暮色中,留下壮丽的夕阳背景。
我的心情一阵莫名的激动。儿时熟稔的景致,如同油画,早已刻印在记忆深处。或许还要继续背负前行,直到叶落归根,回到出发的地方。
母亲细碎的脚步声传来:“还不回家去,天有些凉了。”母亲的两只手不停地擦拭围裙,那是烟火熏的泪花,以及儿子回家的喜悦。我慢慢转身。父亲也回来了:“我说眼皮咋那么跳,寻思一定有啥事,没承想……”我递给父亲一支香烟,父亲拿在手上,还想说什么。母亲催促道:“快去村头看看,能否弄两个小菜。”我赶紧阻止,父亲的背影已消失在错落有致的村舍。
我坐在锅灶前,扯着风箱,一边往灶里填柴草,一边听母亲唠叨,东家长西家短。灶膛里的芝麻秆大豆秸噼里啪啦燃烧,母亲在灶台锅里贴饼。父亲脚步重重地回来,手里拎个竹篮。我伸头一看,竟有活蹦乱跳的小鱼。“你从哪儿弄的?”母亲问。“巧了!村东头的几个人在河里逮鱼,早已分好了,就剩下这么点小鱼,我全留下了。”父亲脸上漾着笑意。母亲说:“看你粗心大意的,还知道儿子喜欢吃小鱼贴饼。”说着,母亲手脚麻利地忙开了。
新鲜的野生小鱼儿独有的香味,弥漫在烟熏火燎的厨房,也弥漫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是专程回来告诉父亲喜讯的,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47年工作,1958年被错误处理,其后做了28年农民。
“办了离休?”父亲喃喃道。“也算罢了,苦了那么些年。”母亲张罗着一桌饭菜,父亲拿出一瓶散装酒,爷俩喝了起来。
村上饭早,串门的来了。“乖乖,在县委工作,那是大官!”叔叔们惊叹的语气,羞得我脸膛泛红。我仔细解释秘书是办事员,不是官。乡亲们搞不明白,反正认为是官,或者以后会变成官。
16年前。父亲的病情愈来愈重,脑血栓后遗症的所有症状都表现出来。他躺在床上,不能言语,进食也越来越困难,勉强能吃些流食。我几乎动用了所有关系,寻找医生来诊断,却没有效果。父亲的痛苦我无法知晓,只是从他偶尔的眼神里看到生的渴望。只有母亲能够读懂父亲的语言,母亲说,父亲不愿意火葬,想回家。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和哥哥陪父亲回到戴圩,一条乡间小路与浩大水塘交汇的三角地带。陌生的杂树,简陋的瓦房,荒芜的院落,这里曾经是我生活17年的老屋。因为没有人居住,而显得荒凉。乡亲们蜂拥而至,母亲爽朗地说笑,与乡亲们扯家常。父亲的眼睛亮起来,嘴角挂满了笑意。我不断地递香烟给乡亲们。父亲看到他们就像树枝看到树叶,鱼儿回归了河水。这是城市无法给予的最大慰藉,也是我无法赠予的心灵药品。
因为工作,我匆匆赶回县里,留下大哥照看父亲。离开家乡时,颠簸的路上,我回忆了父亲的一生,发现关键词竟是乡村,乡村,还是乡村。新中国成立前工作时,父亲住在村里,在很远的乡里做事。十年后,父亲褪去所有光环,带着一家老小,回到村里。过去的十年全扔在外面,乡村平静地接纳了父亲,仿佛时间静止了,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风光的十年。因为患病,也因为我在城里工作,父亲客居小城数年,心却留在那片长满杂草的老屋、一塘碧水的村居。我知道,这次的回家可能是父亲最后的记忆了,或许就是叶落归根,如叶归于泥土。心里不免黯然神伤。
那天,弟弟带哭腔的声音击垮了我。父亲走了!
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可是无情现实来到之时,我的头脑发蒙,两腿发软。父亲安详地睡了,嘴角挂着平静的微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泪水的我,泪水潸然流下。一种彻骨之痛袭来,我空前地孤立无助。(戴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