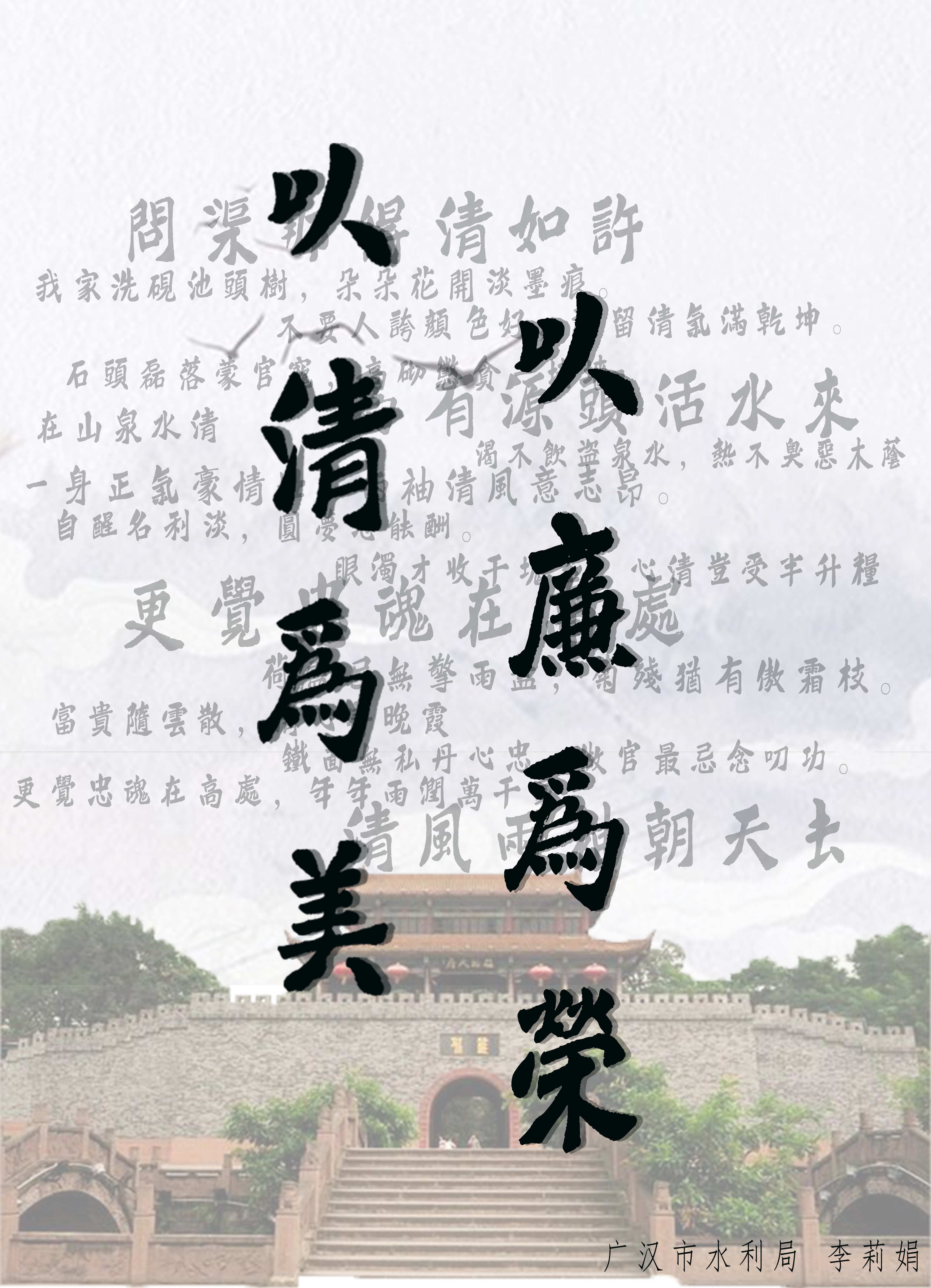乡土之恋
无论我身在何方,在心灵的感悟中,我都是一颗家乡的草籽。乡土中那山那水那人那树———就连春日啼鸣于天空的布谷声声,都像萦绕于怀的音乐图腾,在人生中拂之不去,在梦中与之相依相随。基于这种感悟,穿开裆裤就去了美国读书的小孙儿,几年前从芝加哥大学回国探亲时,正逢电视台为我拍《回家》的专栏节目,我就顺手拉上孙儿,一起回到燕山脚下河北玉田的小小山村。虽然他的母语讲得不错,但在词汇使用上还是闹出了笑话:走进生我养我的房子,他把土炕称之为床;到县宾馆,把做饭的厨师称呼为饲养员。这些跑了调的话语,引起乡亲们的哄堂大笑,致使我不得不为孙儿的语误道歉。之后,我借题发挥开心地说:“我甘当家乡‘饲养员’喂养的牛、马、驴、骡,既愿意为家乡拉犁耕地,更愿意为家乡人驾辕拉车……”
这些笑谈绝非戏言,从我1979年重返文坛之后,家乡的任何一点变化,都能引起我的神经兴奋。生养我的那片故土地下水质特别好,因而酿出的酒浆甘甜浓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家乡生产的啤酒不仅打入京津地区,还留下进入美国白宫的纪录。我兴奋至极,连夜赶写出《种石成玉》的长文,以整版的篇幅发表在《光明日报》,为家乡的巨大发展欢呼喝彩。家乡为此向我求字,我自知书法丑陋,无以回复乡亲之情,先后去过夏衍、艾青、冯牧等文学泰斗的家,请他们为故乡绽的“花朵”题字。岁月已流逝十几个年头,当年夏衍的题字我仍记忆犹新。老人问我家乡有什么典故,我说县志中记载,晋时一位神翁在终南山上种石成玉,故而得名为玉田。夏衍说了声“好”,便挥毫在宣纸上写下“种石成玉”四个大字。老人说:“现代你的家乡,不是演绎了古代‘种石成玉’的神话吗?这几个字非常切题!”令我感伤的是,夏公题字后不久就诀别了人世去了天堂,这幅字字千金的书法可能成了他的绝笔,因而我和我的家乡永生不能忘怀。特别需要提及一笔的是:当时这些大家题字,没有金钱关联———包括后来我引领画家尹瘦石到家乡观光,给家乡留下的诗词墨宝,都是感情的结晶。
可惜的是,这个啤酒厂由于经营不善而每况愈下,濒临倒闭,因而乡恋演变成了乡愁。每逢中秋节同乡聚会于北京,大家都在为家乡的明天献计献策直到深夜。好在故乡水质清纯,虽然垮了啤酒厂,但又站起来声名远扬的白酒厂:玉田老酒不仅被商业部纳入白酒行业中的“中华老字号”,还在文学界演绎出许多有趣的故事。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午夜,我都入睡了,忽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心中有点恼火: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事明天说不行吗,为什么把我从床上折腾起来?后来我的愤懑不仅被对方完全解除,我还哈哈大笑起来。打来电话的是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和《天下无贼》的电影剧本作者王刚,此时此刻他正和《马家军》的作者赵瑜,在北京一个餐馆畅饮玉田老酒呢!酒兴正浓的他,连喊“好酒———好酒”之后,对我讲述了他获得此酒的过程:“从老,我们上个月在茅台酒厂喝茅台时,您向我和麦家讲酒事故事,说到上个世纪之尾王蒙、张洁、国文、心武、莫言、抗抗、晓声等十多个作家在您家豪饮,已故的部队作家叶楠错把玉田老酒当茅台喝了,别人纠正他,他还抱着酒杯不松手。因为您说的这个故事十分有趣,我便记在了心怀。正巧,前两天我开车从北戴河回京,途经您的老家玉田,我就拐进县城买了一瓶玉田老酒,到家一喝就放不下了。再经您老家时,便买了一箱回来。今天找来几个朋友聚会,一起品尝您家乡的美酒。没想到的是,都说是难觅的‘好酒’。于是便给您打去这个电话,给您一个惊喜。是不是……是不是……我打扰您睡觉了?”我高声说:“是睡了,但听到有人夸奖我家乡的‘水’,我的心跳都加速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故乡泥土里生下的一颗草籽、一片树叶。”
我刚要放下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变了声音:“从老,我是赵瑜,喝了您家乡的酒,记起了在我最困难的日子读您的《走向混沌》。之后,我给您写过一封信,说要勇敢地面对生活。这酒就和您的书一样的纯,这么晚了,我还在贪杯……”我说:“那是文坛的真情叙说,你的信我保留至今,希望你义无反顾地关注社会底层,为文学的真实而献身!”
那边又要换人与我对话,我歉意地放下电话———因为这种兴奋延续下去,会让我一夜失眠。我已然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不怕悲悯于怀,只怕兴奋攻心:再要兴奋下去,我怕是要吃安眠药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久久难以成眠,静夜深思,这一切都是乡土情怀引起的。人是不能忘怀故土的,那不仅仅是孕生的根,那还是精神的魂。记得,台湾余光中先生曾写过一首《乡愁》的诗章,那是隔着海峡对大陆故土的相思。我们身在乡土之边,更应该为家乡美好的明天,当一把加薪助燃的干柴———否则就是死了精神基因的孤魂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