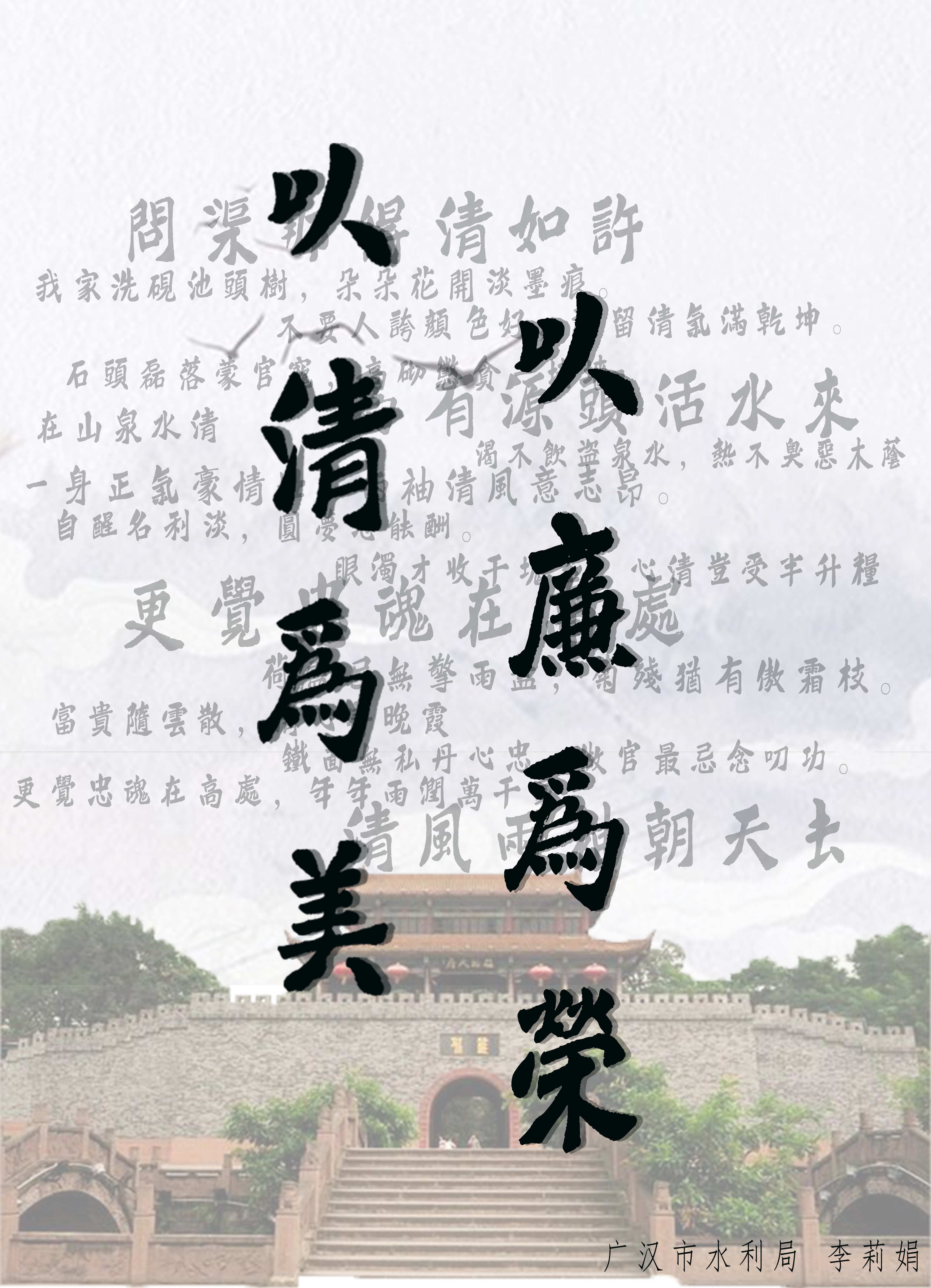走宁夏(上)
一出银川机场,天旷地远,阳光敞亮,刚才还汗津津黏糊糊的胳膊,像用干沙子搓过一样爽净。闷燠的北京给甩远了,它追不上我了,眼下的空间突然无比的阔大。遥望沙碛漫漫,身畔人流熙攘,满眼晃动着由大陆性气候和风沙天气酿造出来的一张张棕色的油性面孔,满耳交响着男女声的“京兰腔”——一种兰州话与北京话嫁接后略带沙音和尘土味儿的普通话,流行于甘宁青新广大地面,听来颇觉亲切。
我知道,在1958年民族区域自治之前,宁夏是甘肃的一个专区。于是,作为离乡多年的甘人,便忽有归家之感。然而,这是错觉,一种却认他乡是故乡的错觉。宁夏这块成吉思汗倾尽全力数次才勉强攻下,且最终因之魂断六盘山的地方,这片以红枸杞、黄甘草、白滩羊、黑发菜驰名于世的塞上沃野,能没有它自己独立而骄傲的历史和现在吗?
银川变得美丽多了,添了好多现代建筑,习习晚风中徜徉于新扩建的“步行街”,有种身在高原的抬升感,如踩高跷一般。前些年我第一次匆匆到银川,只记得灰蒙蒙的天底下,矮平房密密麻麻挤成一簇,只有海宝塔和承天寺塔一西一北高耸云中,遂显得塔愈高而房愈矮。不知那天是我心情不好,还是天阴得重,竟觉得银川老城如一座萧瑟的大村寨。听人说,昔日银川歌谣曰:“一条马路两个楼,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极言其小而寒碜,现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银川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这一带属碱性土壤,远看白茫茫一片,故有此名。又一说是,古代银川一带盛产白银,故而名之。这些说法都于史无证,被当地历史学家推翻了。有记载的一则说法是,前秦苻坚的骢马城就在这一带。骢马是一种青白毛色相间而呈葱白色的名贵骏马,因苻坚是氐族首领,而氐族语又呼骢马为“乞银”,故而放牧“乞银”的地方就叫“乞银城”,后来叫顺了嘴就叫成银川了。这种说法我看倒有几分道理。1928年成立宁夏省,其时银川也叫宁夏城,两个名字重叠,叫起来不方便,需要改。后值蒋介石来宁夏,马鸿逵召集社会贤达拟了“兴中”、“怀远”、“银川”、“兴庆”等四个名字,请蒋挑选圈定。谁知马鸿逵递毛笔时手一抖,蒋没有接住,掉到纸上,可巧就掉到银川二字的头上。蒋很不耐烦地摆手说,勿圈了,勿圈了。遂只得定名为银川,蒋也默认。这传说确否,不得而知,但好玩得很。
去看贺兰岩画的那天,天气晴好,贺兰山在银川城的西北方向若隐若现,勾勒出雾岚似的一溜长线,其幻影似一队骑手控驭着骏马,与我们的汽车并排比赛,车跑多快,它们也跑多快。一查书,果然,“贺兰”乃蒙语骏马之意,看来古人的艺术感觉与我辈并无两样。原以为游人如织,临近时才发现因洪水冲垮了道路,静寂无人。我看见山根下有两座相距不远的玲珑宝塔,颇幽玄,就提出要去。随行的考古专家许先生说,那是有名的拜寺口双塔,当然好看,可惜“看山跑死马”,路也不通,还是看岩画吧。不久,车被鹅卵石窝阻拦,我们只有弃车步行了。忽见一渠由山中蜿蜒而下,水流湍急,用手一试,寒侵肌骨。猛抬头,铁泥堆积似的贺兰群峰背依蓝天近在咫尺,正垂睑俯视着我们,一种旷古岑寂、万年无人的洪荒之感顿袭心头。
所谓贺兰岩画便藏在这数不清的山谷中。我们入一谷,细看沟谷两崖,果有姿态各异的奇怪图案赫然而现。岩刻五花八门,还杂以天书样的西夏文字,其中似人似怪的头像特别多,考古学家说那叫“类人首像”。有一头像毫光四射,听说已被命名为东方太阳神了。动物也多,似有马、驴、牛、羊、鹿、狗、虎、骆驼、鸟等,均在似与不似之间,多半是我瞎蒙的。还有大手印大脚印之类,看多了也烦。
突然,我发现一幅画煞是有趣,画中人做骑马蹲裆式,左手抡一老虎样野兽,右手抡一不明武器,颇有点洪教头式的逞能。许先生凑过来一看说,这是在跳舞呢。经他指点,我慢慢看出点门道了,发现画中人或做弯弓射箭状,或做挥鞭牧羊状,或做操戈刺杀状,还真够多样化的。我无法想象,是何人于何时用何种工具刻制了如此多的奇怪图形。许先生说,它们是古代游牧于贺兰山一带的北方诸民族的生活风俗和精神崇拜的写照。目前国内发现岩画的地方不少,但论学术价值,论文化意蕴的复杂和深邃,皆不能与贺兰岩画相比。但它不是同一时期、同一民族的创作。比如这条沟里,南面崖上多狩猎形态、裸体人形,比较早;北崖有西夏文字,就比较晚。至于年代,迄无定论,因山体类花岗岩型,用再硬的石头也刻画不出来,必须用金属钝器,甚至必须是铁器,所以不会早于春秋战国。对于年限,我这门外汉却有些不同看法,我总觉得它的上限要早得多,早到新石器乃至旧石器时代才对。古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可以攻,石何能例外?我见过上古人类的特种石斧,不明兽骨制成的尖锥,还有天上掉下来的陨铁做成的石钺,其锋利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许先生是考古专家,也是最早的岩画研究家,据他说,贺兰岩画的发现过程还有段曲折呢。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兰州军区某部拉练进入贺兰山中。一日小憩时,一战士坐在石头上边喝水边啃干馍,忽低头发现他屁股下面的石头上有怪异图案,赶紧报告排长,排长也迷惑,只来得及向连长报告,部队就开拔了。后文物部门得到消息,却怎么也找不到,每每入山茫然。遂特意请出那位小战士,让他回忆带路。可惜遍山搜索,不辨旧径,他也迷了路。最后岩画毕竟找到了,但是否还是那条山沟的,已不得而知。这过程很有趣,我怕是许先生编的小说家言,追问确否,他咬定说是真的。他还说贺兰山神秘啊,它藏着大量我们想不到的东西。1984年夏天发洪水,有条山沟里竟冲出了一大罐铜钱,罐重近三百斤,内装三万多枚古钱,从西汉的“半两”到西夏的“光定”全有,你说神奇不神奇?
我还是被岩画之谜吸引着,不由遥想上古游牧人,顶风冒雪,辗转深山荒滩,日夜与牛羊为伴,好不孤单,那种欲与天、地、人、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难以抑制,却又苦无对象,于是以凿刻为语言,把原始的思维和郁积于胸的怒吼注入了这万古不灭的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