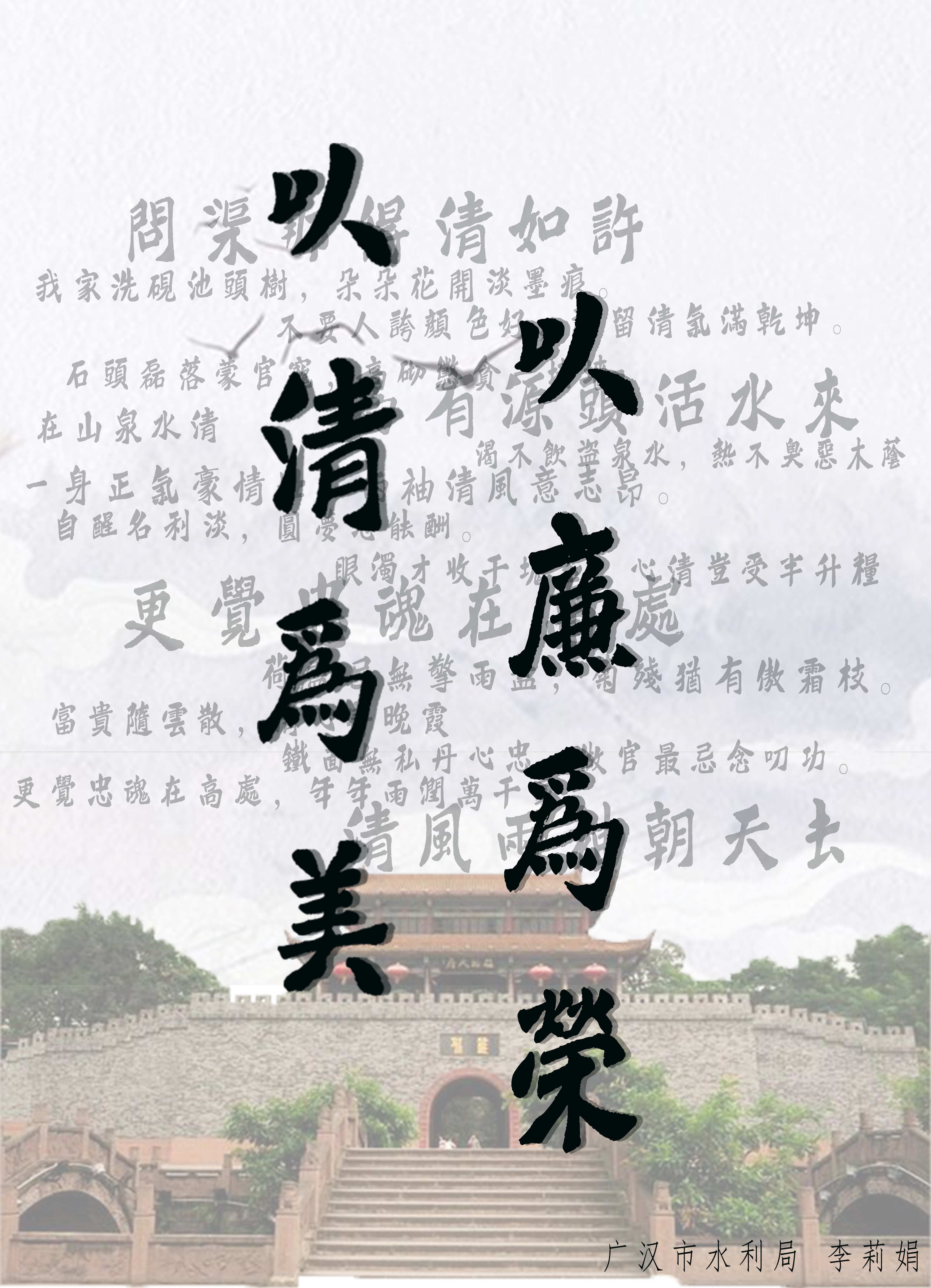与灵魂合影
我有一张颇为自珍的照片,是自拍的,上面也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向来把它夹在合影的影集里。
时隔多少年了,这张照片的产生过程还是那样刻骨铭心。那一年暑假,我凭仗着少年的蛮勇,骑着自行车登上了考察鄂尔多斯高原的征程。时逢盛夏,关陇一带正逢多年不遇的亢旱。从关中通往塞北的大道上,绿色渐趋淡薄,枯黄愈积愈厚。高天里整日悬着一颗大太阳,铮铮作响的光芒,把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晒成一块干土坷垃,用手一捏就会散碎不可收拾。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我终于闯进了榆林县境。
天色已是黄昏,我蹬着自行车沿着一条不知干枯了多少日月的无定河支流河道向北进发。残余的阳光与黄沙的金光互相辉映着,处处都是一派辉煌的光焰。突然间,天地同时昏暗,只听得几声炸雷在头顶轰响,紧接着是一串串撕天裂地的闪电。一阵冷风袭过,我浑身痉挛:暴风雨片刻将至!从小生活在黄土沟壑中的我是深知洪水之迅猛剧烈的,在如此窄狭的古河道上,洪水将会毫不留情地毁灭一切。我遥望前面有一处河岸较为平缓,准备从那里爬上去躲避洪水。我驱车狂奔,行不到数十米,只听得“噗”的一声,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爬起来一看,车胎被尖石扎破了。我推着车子正在踉跄,只听“哗”的一声,宛如天河大堤决口,一瞬间,落在地上的雨水已埋住了脚面。伴随暴雨的是旋风,我想弃车逃命,结果只能在原地兜圈。河道里已能隐约听见洪水摧动石块的厉音,我暗道:这下完了。绝望中,我听到一个声音,那是人的呼唤声:“快往这边靠……”本能使我一手提起车子,一下子倚住了河岸沙壁,只觉得有一只大手将我和车子提了上去。
救我的是一位老人,他在这里烧石灰。他有一顶千疮百孔的小帐篷,帐篷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雨水,只有地铺还未淋湿。他的衣服也湿透了,他让我蹲在地铺上,并将唯一的破棉被披在我身上。他冷冷地问:“干什么的?”“考察的。”“考察什么?”“民情风俗。”“捞了多少钱?”“没捞钱,盘缠都是自己掏的。”经过简约的一问一答,在昏暗的马灯下,我发现老人那凌厉的目光和软了。他又看了我一会儿,说:“还没吃饭吧,想吃点什么?”“没吃饭,也不吃,能避风挡雨就不错了。”老人不再说话,他从地铺下抽出小铁锅,加了半锅水,又取出半碗小米倾在锅里,然后从用塑料布包着的柴火捆里抽出几根干柴燃着了火。在这过程中,他只淡淡地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一进河道,我就看见你了。”我说:“谢谢老人家的救命之恩。”他没有答话,直到柴火燃起来以后他才说:“这是什么话。”
喝过小米粥,身上暖和起来。外面的暴雨正猛,暴风也正狂,河道的洪水将这座小山包震撼得微微颤抖。帐篷也像颠簸在波峰浪谷的小舟,随时都会倾覆。老人将我安顿在唯一的一隅避雨处,他的后背却迎着帐篷的一个破洞,雨滴不时从他的发梢上滚落下来。我多次要求和他换位置,他都以岿然不动的姿态拒绝。当他听了我有自费考察偏远地区人民生存状况的愿望后,脸上第一次绽出笑容。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他家住陕北绥德县农村,自小靠錾石磨手艺游走于北方农村。后来,机器代替了石磨,錾磨手艺没用了,他又出门替人烧石灰。眼下伙伴都回家收麦,留下他看场,把剩下的石灰卖完,他也可回家了。他从帐篷的破洞中向外望了一会儿,有些兴奋地说,今年小麦收成不好,赶上这场大雨,还能抢种一茬秋糜子呢。他双手互相用力地搓着,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经历过的世事完全可以写几本厚书,他简约的讲述,几乎每一句都可与哲人警句相通。我不由得打开了微型录音机。他看见这个精致的小玩意儿问是干啥用的,我说是录音机,并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放了几句。他高兴得脸颊发红,神态也有些忸怩起来。
我俩听着暴风雨和洪水的喧哗整整畅谈了一夜。天亮了,雨也戛然停了,天地一片清新。面前的河道已全然不似昨日面目,河滩里堆满了仿佛凭空而来的巨石。与老人道别时我提出要与老人合一张影。他一下子高兴得不知所措,双手来回搓着说,我还没有照过相呢。我让他先坐在帐篷门口,摆好相机,发现他的脸色庄严得像即临战阵的将军。我按动快门,奔过去与他依偎在一起,咔嗒一声,我想我俩在这样一个暴风雨过后的早晨便成为永恒了。我俩互换了地址,他说无论谁先回家就即刻写信通知对方。他从怀中摸出旱烟锅,装满烟丝,打着火,先抽了一口,然后双手递给我,我凛然一惊,急忙双手接过烟锅。这可是这一带男人间最尊贵的礼节,从此,两人间的承诺就是永不可违的天理。如果一方因故不能如约,那么,子子孙孙都有替先人兑现的义务;而假若一方背约,那么,你在道德上、在灵魂上就永远有着一个亏欠。
一个月后,我在行程五千公里后回家了,打开信箱一看,有一封来自绥德的信。老人在别人替他写的信中陈述了我俩的友谊,并表达了他对照片的急切盼望之情。我深知这张照片在老人人生中的分量,便直奔照相馆,将一大堆胶卷交给了师傅。
可是,当我拿到照片后才发现,与老人合影的那个胶卷全部是空白。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给老人回了信,并寄去几根人参,想借此挽回些许我的罪过。
过了一段时间,绥德来信了,还有一张包裹单。老人表示了谢意,并说他一生没资格享用人参,也从无这个想头,因此奉还给我,唯有那张照片是此生最令他心动的向往,既然皇天不佑,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老人的失望之情跃然纸上,我的心在颤抖。我可是双手接过了老人双手递来的烟袋,那可是鄂尔多斯男人间最尊贵的承诺!我决定,第二天带着相机直奔绥德。
可就在当天晚上,单位领导让我第二天就去南方出差。一个月后,我找着了老人居住的小山村,说明来意后,老人的家人盛情款待了我。饭后,家人才说,老人已去世20天了,那晚受了风寒,回家后就一病不起,临终还在念叨着他的照片。我无言而泪雨如注。
时近黄昏,夕阳与黄沙相映成满天满地的绚晕。我双手捧着相机,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老人的坟茔。老人的灵魂一定还未走远,我相信,我与老人的灵魂于此真正地相会了。(马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