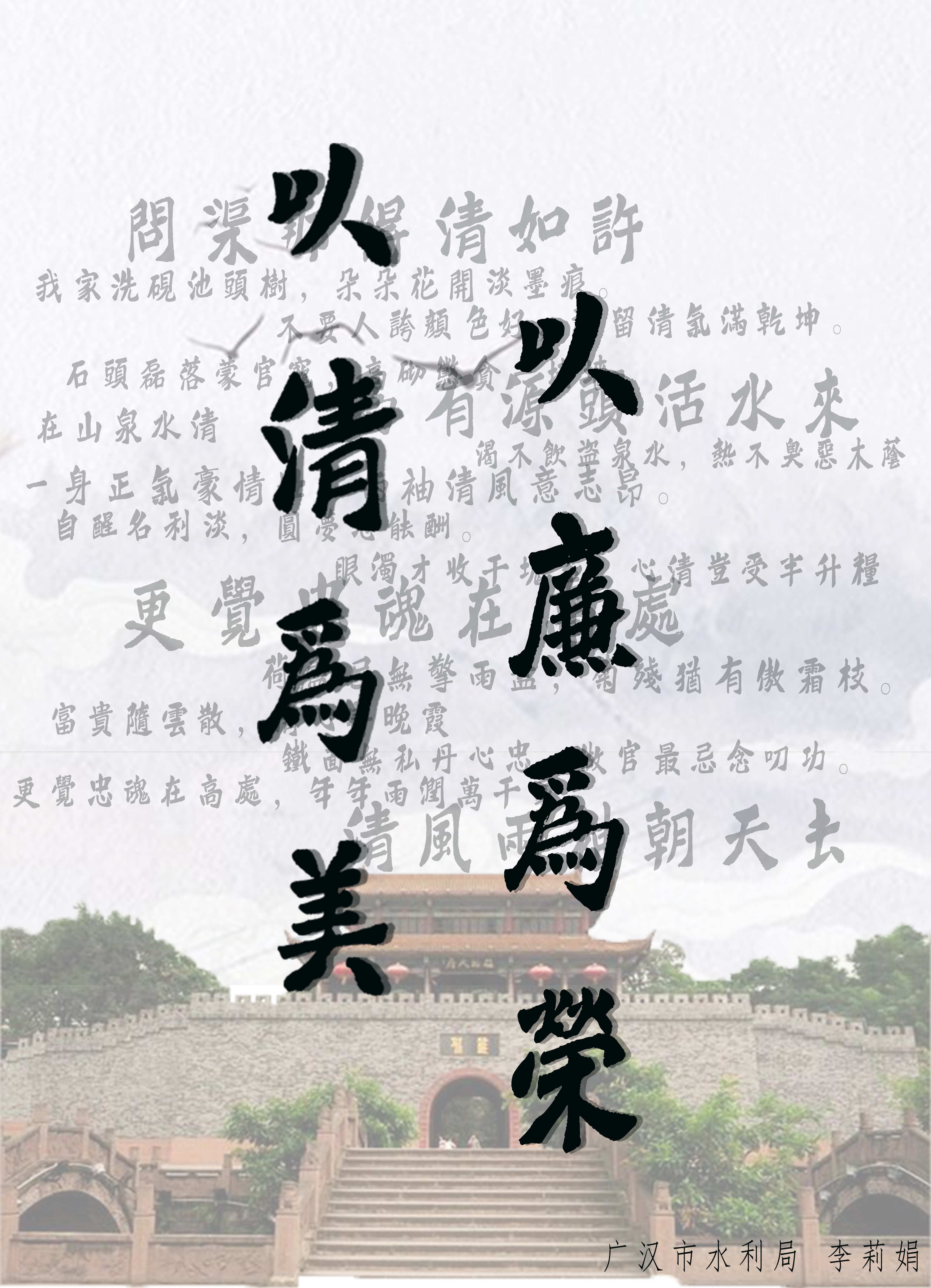我所认识的范曾和我所理解的流水作业
古人讲:读书之功焉可少哉!未有不学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能超越名贤者。我的同学范曾就是这样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范曾于中央美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他对我说:“滕文金,请你到我宿舍帮我搬家。”我想,作为一般同学,不会有什么多重的东西。但是我一提他的皮箱,年轻力壮的我却就是提不动他的箱子。我问范曾:“你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这么重?”他说:“我忘记告诉你了,里面装的全是背诗卡片。”天哪!原来如此。我问他:“你究竟背了多少首诗?”他说:“从古至今的每个大诗人选二十首,总计背了五六千首。”于是油然而生敬意。我不是敬佩他的记忆力,而是由衷地被他的毅力所折服。范曾说:“滕文金,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中等智力。”我心想,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足使我望尘莫及了。范曾的床上还有一捆每卷像食指那么粗细的宣纸卷,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临摹的从古至今的白描作品,可以说历史上所有的白描作品我都临摹过。”谈到临摹作品时,范曾不无感慨地说:“最难临摹的就是为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临南宋李嵩的《货郎图》,那些小玩意足有三百多种,现在我都临不了了啊。”
因为我是新中国首钢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出身,中小学都没有读过,所以想在中央美院六年的大学学习中都补上。但由于我废寝忘食,结果到三年级时,我却因劳累过度造成失眠。医生说我是患了神经衰弱症。这时我认识了同校不同班系的范曾,他说:“你这小子尽学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搞艺术的只学两样就够了:一是文学,二是基本功。”我问他:“你告诉我怎么学?”他说:“你跟我学,每天早起二个小时背唐诗宋词,待同学们六时起床时我们已经学了两个小时了。”我的文学基础就是在校后三年打下的。后来范曾又教我练毛笔字。很遗憾,我只认为文学和我从事的雕塑最重要,因此未能像范曾那样去习书法。而范曾却是历史、文学、书法、绘画,四样并进,并学有所成。后来范曾对我说:“毕业之后我曾向一位书法家学了二十年。我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一百多遍,一百零一遍时专门向郭沫若先生请教。郭老说我临的《兰亭序》是真假难分了。”以后范曾对我说:“我练字练了四十年,现在才练出我自己的字。”中央美院毕业时,我专门创作了范曾肖像雕像赠给范曾,后来范曾又专门为我画了肖像,至今我仍然珍存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中央美院几位老同学聊天,女画家周思聪问我:“滕文金,你说在咱们同学中有谁诗、书、画全能?不就是范曾么?有些同学妒忌他的画卖得贵,真没有必要。”蒋兆和老先生唯一的研究生马振声说:“滕文金,我与你说吧,诗书画不能说范曾都是最好的,但三者加起来,他就是总冠军!”七十岁以后的范曾,不但还能把唐宋诗词记得滚瓜乱熟,而且还能把屈原的《离骚》背诵的一字不差!
歌德曾说过,要在世界上划一个时代,要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条件,第一要有一副好头脑,其次要继承一份巨大的遗产。有一次,范曾对我说:“我在台湾画国父孙中山,事先看了照片,将形象记在心里,到现场一画而就,在场的人都惊绝!”凭记忆画人物肖像,画得如此形神兼备,怎能不令人心服口服!范曾画弘一法师、黄宾虹等大师时,都是仅凭记忆一画而就,从不边看边画,也从未改来改去。范曾真正做到我们老院长吴作人先生说的“手眼脑达到高度一致的学生。”所以范曾作画时,如同秋风扫落叶,特快。有一次我去他家吃饭,饭前他给我画了一幅“孔乙己坐在地上小杯饮酒”的画。饭后他说:“画错了,你小子还真能喝,再给你重画一幅。”没有几分钟他就给我又画了一幅“鲁智深捧着大罐子在狂饮”的画。范曾画画从不用铅笔打草稿,都是用毛笔一挥而就。这说明他画画从来都是“胸有成竹”。
中国人历来就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所谓誉来而谤兴。近年来有人诋毁范曾作画是“流水作业。”何谓“流水作业?”我在首都钢铁公司六年,曾学铸造两年,深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何谓流水作业。”钢铁公司首先是勘探矿场,其次是开采,然后运输到炼钢厂,到厂后再选矿和筛选,再运送到炼铁炉,铁水炼出来后再送电炉厂冶炼钢,然后再铸成钢锭。这才完成初级钢材。因用途不同还要再加料再练成不同用途的钢。你说这吨钢是谁的作品?谁的都不是,但又是每道工序都不能缺的,是千百万人共同心血的结晶。可以这样说,工业生产基本上都是流水作业。因此也就不能署名。而范曾的绘画,同样一个题材,一次同时画十幅,只能说他有一颗好大脑,记忆力盖世无双,这是一般画家望尘莫及的。谁能画过画再连续画多幅,当然每幅他都会有小的区别,只有他自己有意而为之。所以你说他毫无区别,只能是眼拙而已。
文章开头我说范曾诗书画的功力,完全有能力画出一模一样的作品,但他每幅画都会有新的追求。记得当年李可染先生给我们讲课时,要求我们读画时不要光看,要精读。比方拿范曾的《老子出关》作品来说,老子、青牛、小孩,题材和构图看似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你细读的话,总会分出每幅画的线条粗细、墨的浓淡和笔力的轻重是有区别的。如果真的毫厘不差,那更是难得的作品。但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人不是机械。所以说题材和构图的重复不等于流水线的产品。苹果手机是流水线的产品,因为它的每个机件要统一,都不能有误差,否则它就组装不起来。
再说一个画家的题材是有倾向性的,如齐白石老人的虾,徐悲鸿先生的马,吴作人先生的熊猫,黄胄先生的驴等,请注意他们的作品都不是白描。而白描对于绘画来说是基础,但它又是最难掌握的。几根线要体现出空间来确实很难。罗丹说要使每根线都在游动,这点范曾做到了。日本人专门为范曾建造“范曾美术馆”,就是看了范曾的画,感觉每个人物都从画面上走出来了。就是说范曾把白描用活了。同时因为白描是赤裸裸地,也给人一种简单的感觉,也或是重复的感觉。但这与流水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范曾作品的多产,应该说是他厚积薄发。似乎于简练的东西使人难以理解,歌德说:愈不易凭知解力去理解,也就愈好。(滕文金)